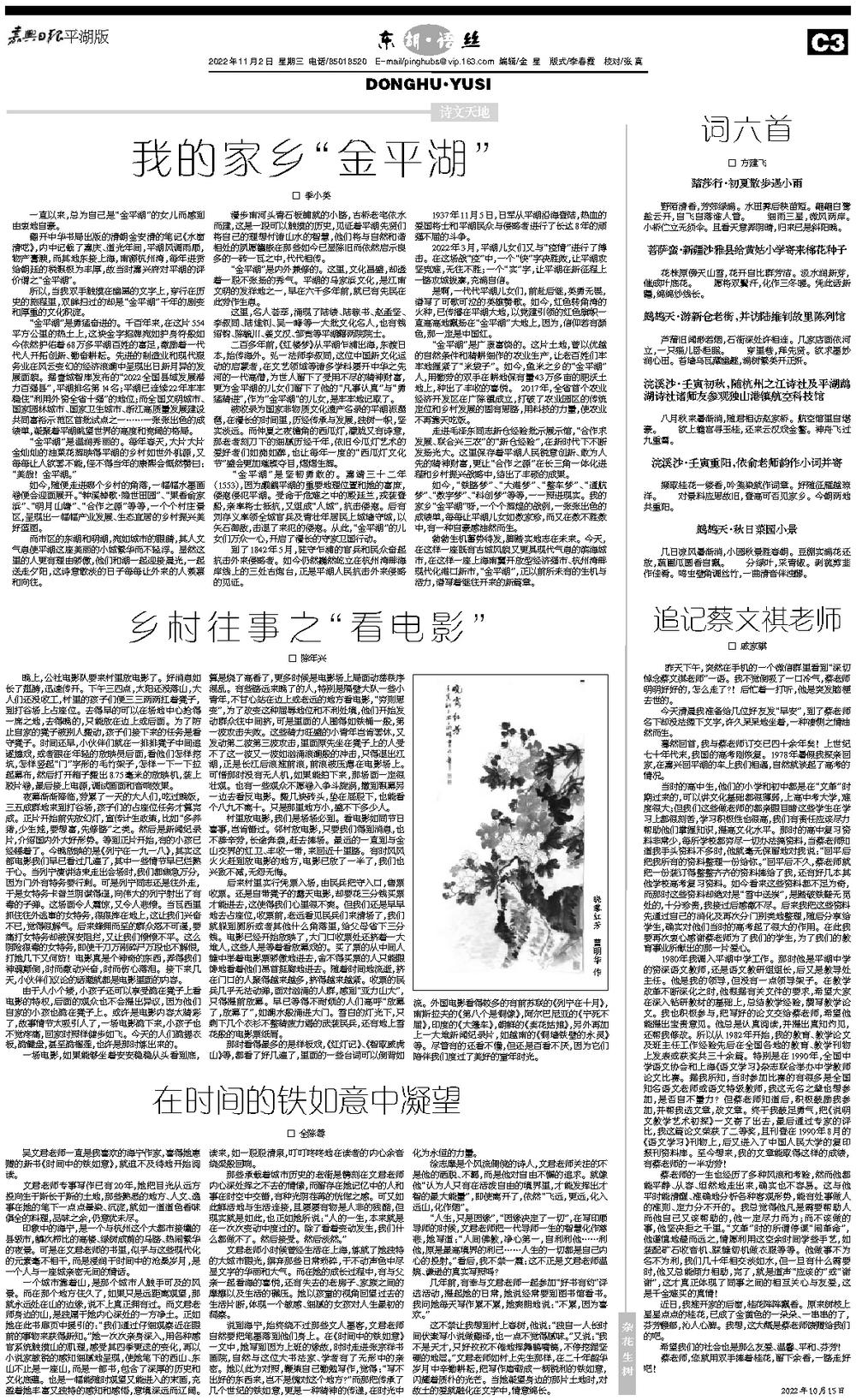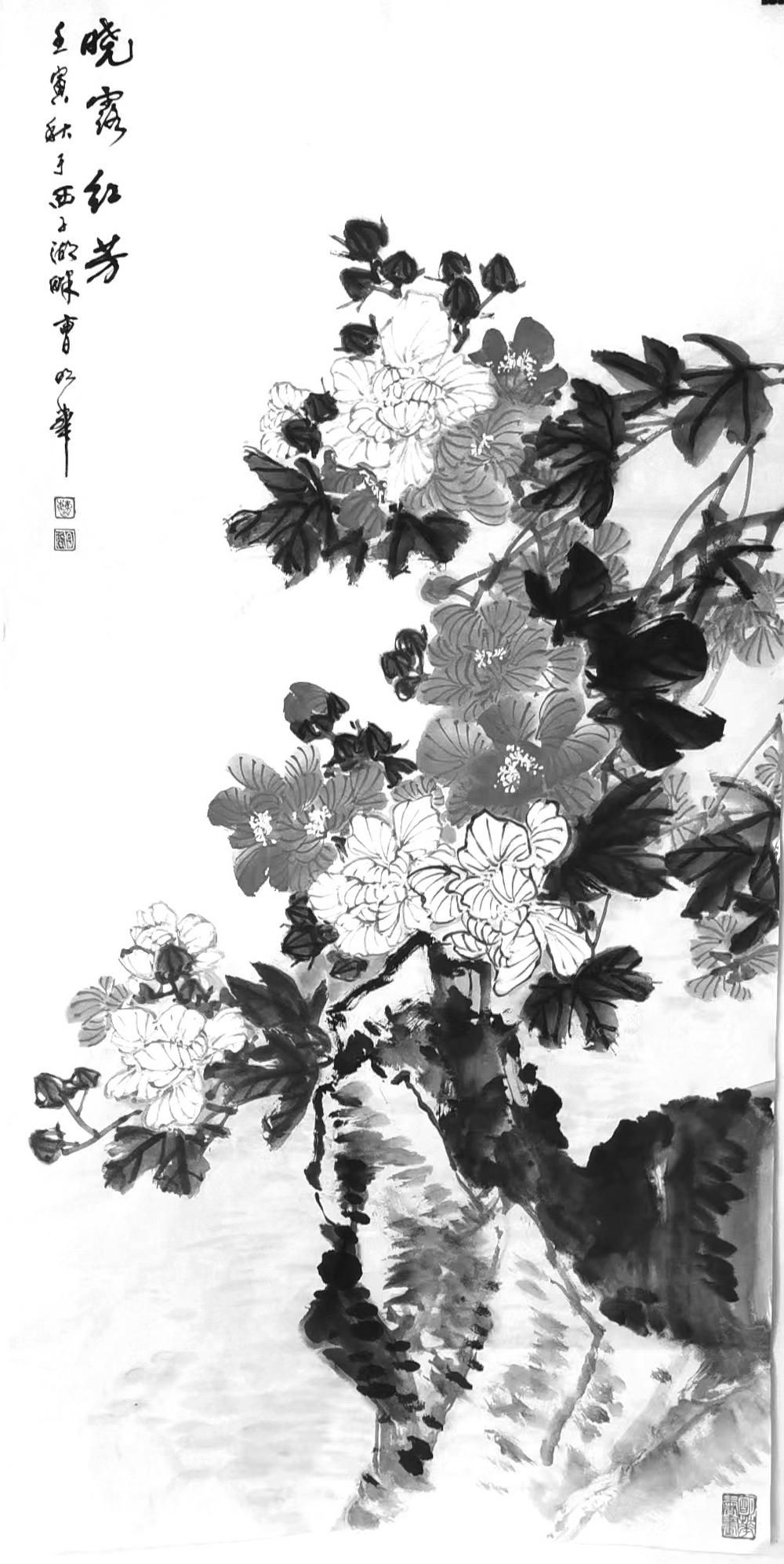□ 陈年兴
晚上,公社电影队要来村里放电影了。好消息如长了翅膀,迅速传开。下午三四点,太阳还没落山,大人们还没收工,村里的孩子们便三三两两扛着凳子,到打谷场上占座位。去得早的可以在场地中心抢得一席之地,去得晚的,只能放在边上或后面。为了防止自家的凳子被别人搬动,孩子们接下来的任务是看守凳子。时间还早,小伙伴们就在一排排凳子中间追逐嬉戏,或者跟在年轻的放映员后面,看他们怎样挖坑,怎样竖起“门”字形的毛竹架子,怎样一下一下拉起幕布,然后打开箱子搬出8.75毫米的放映机,装上胶片卷,最后接上电源,调试画面和音响效果。
夜幕渐渐降临,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吃过晚饭,三五成群地来到打谷场,孩子们的占座位任务才算完成。正片开始前先放幻灯,宣传计生政策,比如“多养猪,少生娃,要想富,先修路”之类。然后是新闻纪录片,介绍国内外大好形势。等到正片开始,有的小孩已经睡着了。今晚放映的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其实这部电影我们早已看过几遍了,其中一些情节早已烂熟于心。当列宁演讲结束走出会场时,我们都焦急万分,因为门外有特务要行刺。可是列宁同志还是往外走,于是女特务卡普兰阴谋得逞,向伟大的列宁射出了有毒的子弹。这场面令人震惊,又令人悲愤。当瓦西里抓住往外逃窜的女特务,狠狠摔在地上,这让我们兴奋不已,觉得很解气。后来蜂拥而至的群众怒不可遏,要痛打女特务却被保安阻拦,又让我们愤愤不平。这么阴险狠毒的女特务,即使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也不解恨,打她几下又何妨!电影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弄得我们神魂颠倒,时而激动兴奋,时而伤心落泪。接下来几天,小伙伴们议论的话题就都是电影里面的内容。
由于人小个矮,小孩子还可以享受跪在凳子上看电影的特权,后面的观众也不会提出异议,因为他们自家的小孩也跪在凳子上。或许是电影内容太精彩了,故事情节太吸引人了,一场电影跪下来,小孩子也不觉疼痛,回家时照样健步如飞。今天的人们跪搓衣板,跪键盘,甚至跪榴莲,也许是那时练出来的。
一场电影,如果能够坐着安安稳稳从头看到底,算是烧了高香了,更多时候是电影场上局面动荡秩序混乱。有些路远来晚了的人,特别是隔壁大队一些小青年,不甘心站在边上或老远的地方看电影,“穷则思变”,为了改变这种屈辱地位和不利处境,他们开始发动群众往中间挤,可是里面的人围得如铁桶一般,第一波攻击失败。这些精力旺盛的小青年岂肯罢休,又发动第二波第三波攻击,里面原先坐在凳子上的人受不了这一波又一波如汹涌浪潮般的冲击,只得退出江湖,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压瘪在电影场上。可惜那时没有无人机,如果能拍下来,那场面一定很壮观。也有一些观众不愿卷入争斗旋涡,撤到银幕另一边去看反电影。搬几块砖头,垫在屁股下,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只是那里地方小,盛不下多少人。
村里放电影,我们是场场必到。看电影如同节日喜事,岂肯错过。邻村放电影,只要我们得到消息,也不辞辛劳,长途奔袭,赶去捧场。最远的一直到与金山交界的红卫、丰收一带,来回近十里路。有时风风火火赶到放电影的地方,电影已放了一半了,我们也兴致不减,无怨无悔。
后来村里实行凭票入场,由民兵把守入口,售票收票。还是自带凳子的露天电影,却要花三分钱买票才能进去,这使得我们心里很不爽。但我们还是早早地去占座位,收票前,老远看见民兵们来清场了,我们就躲到厕所或者其他什么角落里,给父母省下三分钱。电影已经开始放映了,大门口收票处还挤着一大堆人,这些人是等着看放幕戏的。买了票的从中间人缝中举着电影票骄傲地进去,舍不得买票的人只能眼馋地看着他们昂首挺胸地进去。随着时间地流逝,挤在门口的人聚得越来越多,挤得越来越紧。收票的民兵几乎无法动弹,面对汹涌的人群,感到“亚力山大”,只得提前放幕。早已等得不耐烦的人们高呼“放幕了,放幕了”,如潮水般涌进大门。雪白的灯光下,只剩下几个衣衫不整精疲力竭的武装民兵,还有地上雪花般的电影票纸屑。
那时看得最多的是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都看了好几遍了,里面的一些台词可以倒背如流。外国电影看得较多的有前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南斯拉夫的《第八个是铜像》,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印度的《大篷车》,朝鲜的《卖花姑娘》,另外再加上一大堆新闻纪录片,如越南的《铜墙铁壁的永灵》等。尽管有的还看不懂,但还是百看不厌,因为它们陪伴我们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
晓露红芳 曹明华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