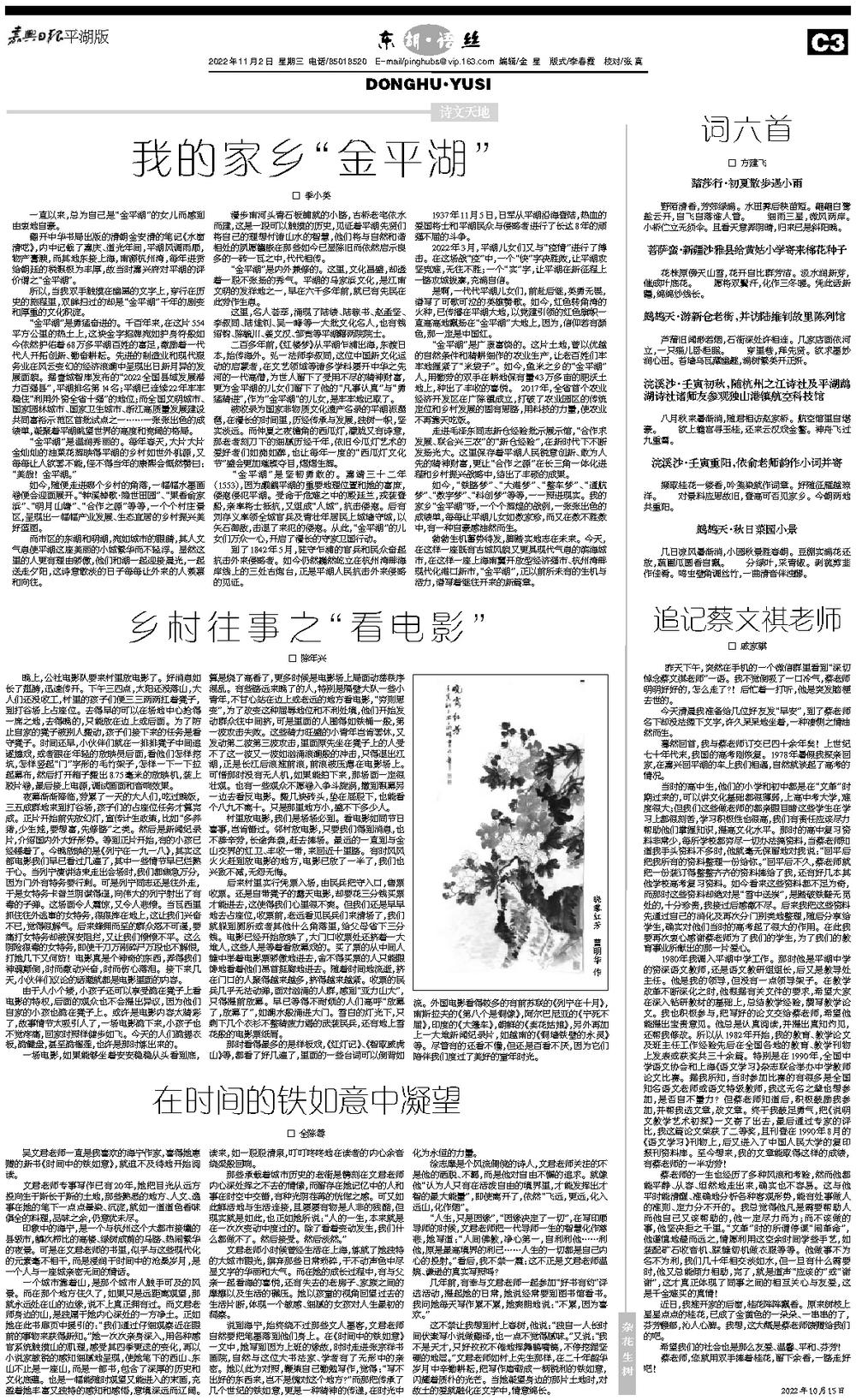□ 全陈蓉
吴文君老师一直是我喜欢的海宁作家,喜得她惠赠的新书《时间中的铁如意》,就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
文君老师专事写作已有20年,她把目光从远方投向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那些熟悉的地方、人文、逸事在她的笔下一点点晕染、沉淀,就如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料理,品味之余,仍意犹未尽。
印象中的海宁,是一个与杭州这个大都市接壤的县级市,鳞次栉比的高楼、绿树成荫的马路、热闹繁华的夜景。可是在文君老师的书里,似乎与这些现代化的元素毫不相干,而是浸润于时间中的沧桑岁月,是一个人与一座城亲密无间的情话。
一个城市靠着山,是那个城市人触手可及的风景。而在那个地方住久了,如果只是远距离观望,那就永远处在山的边缘,说不上真正拥有过。而文君老师身边的山,是独属于她内心深处的一方净土。正如她在此书扉页中援引的:“我们通过仔细观察近在眼前的事物来获得新知。”她一次次亲身深入,用各种感官系统触摸山的肌理,感受其四季更迭的变化,再以小说家敏锐的感知细腻地呈现,使她笔下的西山、东山不止是一座山,而是一部书,包含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也是一幅能随时观望又能进入的宋画,充盈着她丰富又独特的感知和感悟,意境深远而辽阔。读来,如一股股清泉,叮叮咚咚地在读者的内心余音绕梁般回响。
那些承载着城市历史的老街是镌刻在文君老师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情愫,而留存在她记忆中的人和事在时空中交错,有种光阴荏苒的恍惚之感。可又如此鲜活地与生活连接,且屡屡有物是人非的残酷,但现实就是如此,也正如她所说:“人的一生,本来就是在一次次变动中度过的。除了看着变动发生,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然后接受。然后淡然。”
文君老师小时候曾经生活在上海,练就了她独特的大城市眼光,摒弃那些日常琐碎,于不动声色中尽显文字的华丽和大气。而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有与父亲一起看海的喜悦,还有失去的老房子、家族之间的摩擦以及生活的碾压。她以孩童的视角回望过去的生活片断,体现一个敏感、细腻的女孩对人生最初的洞察。
说到海宁,始终绕不过那些文人墨客,文君老师自然要把笔墨落到他们身上。在《时间中的铁如意》一文中,她写到因为上班的缘故,时时走进张宗祥书画院,自然与这位大书法家、学者有了无形中的亲密。她以此为对照,鞭策自己勤勉写作,觉得:“写不出好的东西来,岂不是愧对这个地方?”而那把传承了几个世纪的铁如意,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在时光中化为永恒的力量。
徐志摩是个风流倜傥的诗人,文君老师关注的不是他的洒脱、不羁,而是他对自由不懈的追求。就像他“认为人只有在活泼自由的境界里,才能发挥出才智的最大能量”,即使离开了,依然“飞远,更远,化入远山,化作烟”。
“人生,只是因缘”,“因缘决定了一切”,在写印顺导师的时候,文君老师把一代导师一生的智慧化作慈悲,她写道:“人间佛教,净心第一,自利利他……利他,原是最高境界的利己……人生的一切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射。”看后,我不禁一震:这不正是文君老师温婉、谦逊的真实写照吗?
几年前,有幸与文君老师一起参加“好书有约”评选活动,提起她的日常,她说经常要到图书馆看书。我问她每天写作累不累,她爽朗地说:“不累,因为喜欢。”
这不禁让我想到村上春树,他说:“独自一人长时间伏案写小说做翻译,也一点不觉得腻味。”又说:“我不是天才,只好孜孜不倦地挥舞鹤嘴镐,不停挖掘坚硬的地层。”文君老师如村上先生那样,在二十年韶华岁月中辛勤耕耘,把写作磨砺成一柄锐利的铁如意,闪耀着质朴的光芒。当她凝望身边的那片土地时,对故土的爱就融化在文字中,情意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