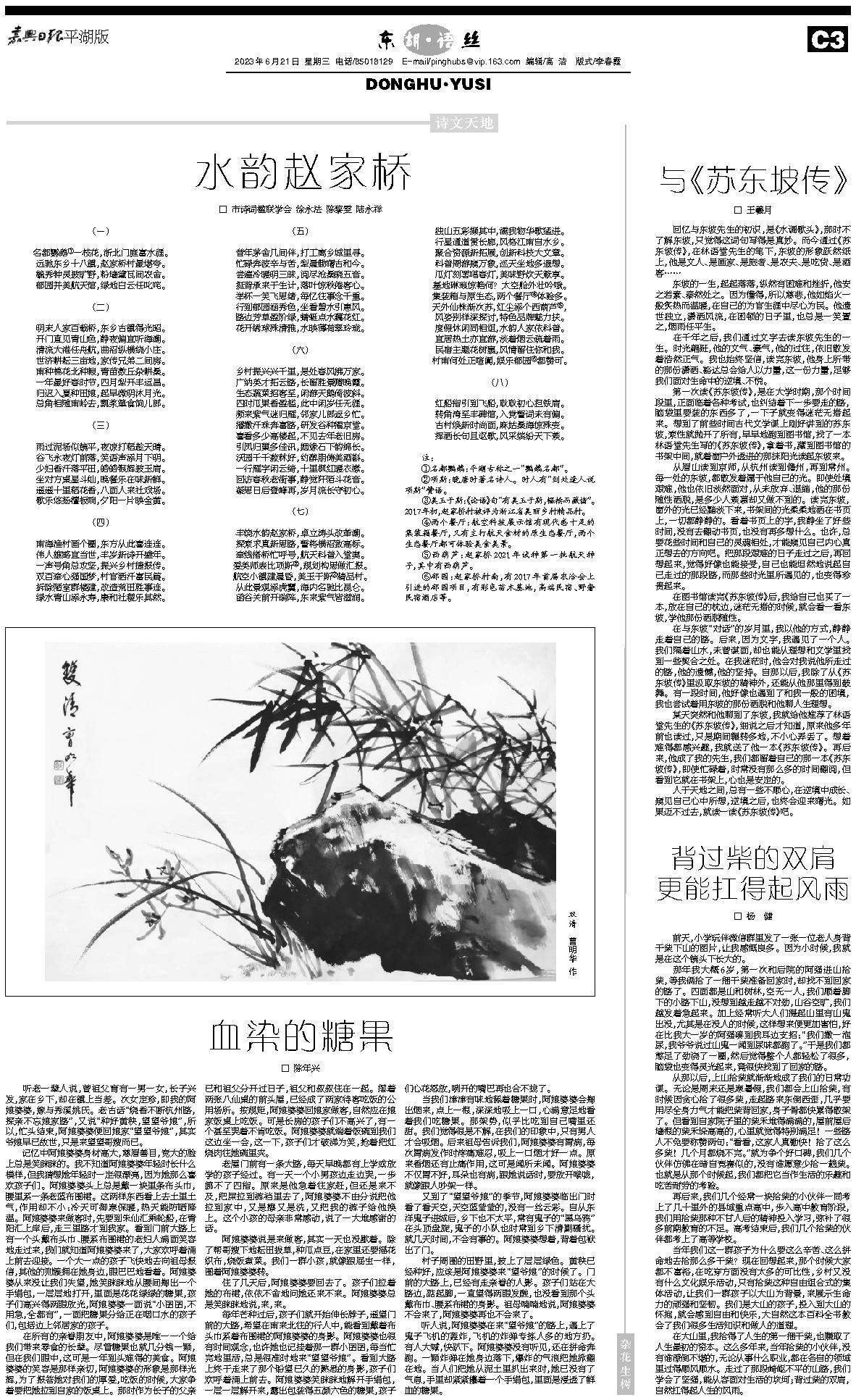□ 陈年兴
听老一辈人说,曾祖父育有一男一女,长子兴发,家在乡下,却在镇上当差。次女定珍,即我的阿娘婆婆,嫁与秀溪姚氏。老古话“烧香不断杭州路,探亲不忘娘家路”,又说“种好黄秧,望望爷娘”,所以,忙头结束,阿娘婆婆便回娘家“望望爷娘”,其实爷娘早已故世,只是来望望哥嫂而已。
记忆中阿娘婆婆身材高大,慈眉善目,宽大的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我不知道阿娘婆婆年轻时长什么模样,但我猜想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因为她那么喜欢孩子们。阿娘婆婆头上总是戴一块里条布头巾,腰里系一条老蓝布围裙。这两样东西看上去土里土气,作用却不小:冷天可御寒保暖,热天能防晒降温。阿娘婆婆来做客时,先要到朱仙汇乘轮船,在青阳汇上岸后,走三里路才到我家。看到门前大路上有一个头戴布头巾、腰系布围裙的老妇人满面笑容地走过来,我们就知道阿娘婆婆来了,大家欢呼着涌上前去迎接。一个大一点的孩子飞快地去向祖母报信,其他的则簇拥在她身边,眼巴巴地看着。阿娘婆婆从来没让我们失望,她笑眯眯地从腰间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层地打开,里面是花花绿绿的糖果,孩子们高兴得两眼放光,阿娘婆婆一面说“小囝囝,不用急,全都有”,一面把糖果分给正在咽口水的孩子们,包括边上邻居家的孩子。
在所有的亲眷朋友中,阿娘婆婆是唯一一个给我们带来零食的长辈。尽管糖果也就几分钱一颗,但在我们眼中,这可是一年到头难得的美食。阿娘婆婆的笑容是那样亲切,阿娘婆婆的形象是那样光辉,为了报答她对我们的厚爱,吃饭的时候,大家争着要把她拉到自家的饭桌上。那时作为长子的父亲已和祖父分开过日子,祖父和叔叔住在一起。摆着两张八仙桌的前头屋,已经成了两家待客吃饭的公用场所。按规矩,阿娘婆婆回娘家做客,自然应在娘家饭桌上吃饭。可是长房的孩子们不高兴了,有一个甚至哭着不肯吃饭。阿娘婆婆就端着饭碗到我们这边坐一会,这一下,孩子们才破涕为笑,抢着把红烧肉往她碗里夹。
老屋门前有一条大路,每天早晚都有上学或放学的孩子经过。有一天一个小男孩边走边哭,一步挪不了四指。原来是他急着往家赶,但还是来不及,把屎拉到裤裆里去了,阿娘婆婆不由分说把他拉到家中,又是擦又是洗,又把我的裤子给他换上。这个小孩的母亲非常感动,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
阿娘婆婆说是来做客,其实一天也没歇着。除了帮哥嫂下地耘田拔草,种瓜点豆,在家里还要摇花织布,烧饭煮菜。我们一群小孩,就像跟屁虫一样,围着阿娘婆婆转。
住了几天后,阿娘婆婆要回去了。孩子们拉着她的布裙,依依不舍地问她还来不来。阿娘婆婆总是笑眯眯地说,来,来。
每年芒种过后,孩子们就开始伸长脖子,遥望门前的大路,希望在南来北往的行人中,能看到戴着布头巾系着布围裙的阿娘婆婆的身影。阿娘婆婆也很有时间观念,也许她也记挂着那一群小囝囝,每当忙完地里活,总是很准时地来“望望爷娘”。看到大路上终于走来了那个盼望已久的熟悉的身影,孩子们欢呼着涌上前去。阿娘婆婆笑眯眯地解开手绢包,一层一层解开来,露出包装得五颜六色的糖果,孩子们心花怒放,咧开的嘴巴再也合不拢了。
当我们津津有味地舔着糖果时,阿娘婆婆会掏出烟来,点上一根,深深地吸上一口,心满意足地看着我们吃糖果。那架势,似乎比吃到自己嘴里还甜。我们觉得很是不解,在我们的印象中,只有男人才会吸烟。后来祖母告诉我们,阿娘婆婆有胃病,每次胃病发作时疼痛难忍,吸上一口烟才好一点。原来香烟还有止痛作用,这可是闻所未闻。阿娘婆婆不仅胃不好,耳朵也有病,跟她说话时,要放开喉咙,就像跟人吵架一样。
又到了“望望爷娘”的季节,阿娘婆婆临出门时看了看天空,天空蓝莹莹的,没有一丝云彩。自从东洋鬼子进城后,乡下也不太平,常有鬼子的“黑乌鸦”在头顶盘旋,鬼子的小队也时常到乡下清剿骚扰。就几天时间,不会有事的。阿娘婆婆想着,背着包袱出了门。
村子周围的田野里,披上了层层绿色。黄秧已经种好,应该是阿娘婆婆来“望爷娘”的时候了。门前的大路上,已经有走亲眷的人影。孩子们站在大路边,踮起脚,一直望得两眼发酸,也没看到那个头戴布巾、腰系布裙的身影。祖母喃喃地说,阿娘婆婆不会来了,阿娘婆婆再也不会来了。
听人说,阿娘婆婆在来“望爷娘”的路上,遇上了鬼子飞机的轰炸,飞机的炸弹专拣人多的地方扔。有人大喊,快趴下。阿娘婆婆没有听见,还在拼命奔跑。一颗炸弹在她身边落下,爆炸的气浪把她掀翻在地。当人们把她从泥土里扒出来时,她已没有了气息,手里却紧紧攥着一个手绢包,里面是浸透了鲜血的糖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