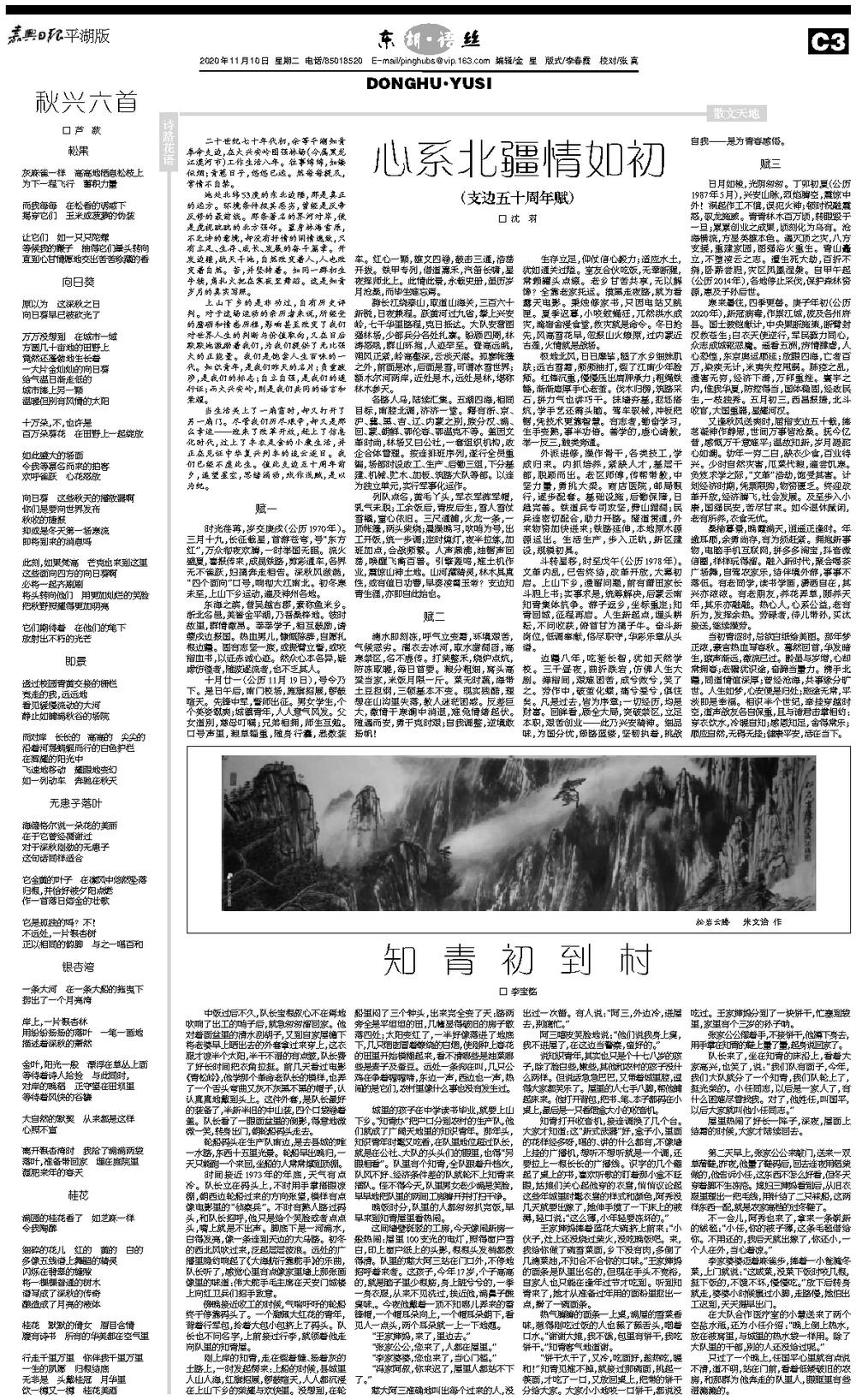□ 李宝铭
中饭过后不久,队长宝根叔心不在焉地吹响了出工的哨子后,就急匆匆溜回家。他对着面盆里的清水刮胡子,又到自家屋檐下将老婆早上晒出去的外套拿过来穿上,这衣服才凉半个太阳,半干不湿的有点皱,队长费了好长时间把衣角拉挺。前几天看过电影《青松岭》,他学那个革命老队长的模样,也弄了一个舌头弯曲又灰不灰黑不黑的帽子,认认真真地戴到头上。这件外套,是队长最好的装备了,半新半旧的中山装,四个口袋卷着盖。队长看了一眼面盆里的倒影,得意地微微一笑,转身出门,朝轮船码头走去。
轮船码头在生产队南边,是去县城的唯一水路,东西十五里光景。轮船早出晚归,一天只能跑一个来回,坐船的人常常撑到顶棚。
时间接近1973年的年底,天气有点冷。队长立在码头上,不时用手掌搭眼凉棚,朝西边轮船过来的方向张望,模样有点像电影里的“侦察兵”。不时有熟人路过码头,和队长招呼,他只是给个笑脸或者点点头,嘴上就是不出声。脚底下是一河满水,白得发亮,像一条连到天边的大马路。初冬的西北风吹过来,泛起层层波浪。远处的广播里隐约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队长听了,感觉心里有点像家里墙上那张画像里的味道:伟大舵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们招手致意。
傍晚接近收工的时候,气喘吁吁的轮船终于停靠码头了。一个胸佩大红花的青年,背着行军包,拎着大包小包挤上了码头。队长也不问名字,上前接过行李,就领着他走向队里的知青屋。
刚上岸的知青,走在裂着缝、扬着灰的土路上,一时发起愣来:上船的时候,县城里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人都沉浸在上山下乡的荣耀与欢快里。没想到,在轮船里闷了三个钟头,出来完全变了天:路两旁全是平坦坦的田,几幢显得破旧的房子散落四处;太阳变红了,一半好像落进了地底下,几只烟囱冒着缭绕的白烟,使刚种上春花的田里开始模糊起来,看不清哪些是油菜哪些是麦子及蚕豆。远处一条狗在叫,几只公鸡在争着喔喔啼,东边一声,西边也一声,热闹的是它们,农村里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城里的孩子在中学读书毕业,就要上山下乡。“知青办”把户口分到农村的生产队,他们就成了广阔天地里的知识青年。那年头,知识青年时髦又吃香,在队里地位超过队长,就是在公社、大队的头头们的眼里,也得“另眼相看”。队里有个知青,全队跟着升档次,队风不好、经济条件差的队就轮不上知青来插队。怪不得今天,队里男女老少满是笑脸,早早地把队里的两间工房腾开并打扫干净。
晚饭时分,队里的人都匆匆扒完饭,早早来到知青屋里看热闹。
这间墙壁斑驳的工房,今天像闹新房一般热闹:屋里100支光的电灯,照得窗户雪白,印上窗户纸上的头影,根根头发梢都数得清。队里的憨大阿三站在门口外,不停地招呼着来者。这孩子,今年17岁,个子高高的,就是脑子里少根筋,身上脏兮兮的,一季一身衣服,从来不见洗过,挨近他,满鼻子酸臭味,。今夜他戴着一顶不知哪儿弄来的雷锋帽,一个帽耳朵向上,一个帽耳朵朝下,看见人一点头,两个耳朵就一上一下地翘。
“王家婶妈,来了,里边去。”
“张家公公,您来了,人都在屋里。”
“李家婆婆,您也来了,当心门槛。”
“冯家阿叔,你来迟了,屋里人都站不下了。”
憨大阿三准确地叫出每个过来的人,没出过一次错。有人说:“阿三,外边冷,进屋去,别瞎忙。”
阿三嘻皮笑脸地说:“他们说我身上臭,我不进屋了,在这边当警察,蛮好的。”
说知识青年,其实也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除了脸白些,嫩些,其他和农村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但说话急急巴巴,又带着城里腔,逗得大家都笑乐了。屋里的人七手八脚,帮他铺起床来。他打开背包,把书、笔、本子都码在小桌上,最后是一只香烟盒大小的收音机。
知青打开收音机,接连调换了几个台。大家才知道:这“新式武器”好,盒子小,里面的花样经多呀,唱的、讲的什么都有,不像墙上挂的广播机,想听不想听就是一个调,还要拉上一根长长的广播线。识字的几个翻起了桌上的书,喜欢听歌的盯着那小盒不眨眼,姑娘们关心起他穿的衣裳,悄悄议论起这些年城里时髦衣裳的样式和颜色,阿秀没几天就要出嫁了,她伸手摸了一下床上的被褥,轻口说:“这么薄,小年轻要冻坏的。”
王家婶妈捧着蓝花大碗挤上前来:“小伙子,灶上还没烧过柴火,没吃晚饭吧。来,我给你做了碗雪菜面,乡下没有肉,多倒了几滴菜油,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王家婶妈的面条是队里出名的,但现在手头不宽裕,自家人也只能在逢年过节才吃到。听到知青来了,她才从准备过年用的面粉里抠出一点,擀了一碗面条。
热气腾腾的面条一上桌,满屋的雪菜香味,惹得刚吃过饭的人也舔了舔舌头,咽着口水。“谢谢大娘,我不饿,包里有饼干,我吃饼干。”知青客气地道谢。
“饼干太干了,又冷,吃面好,趁热吃,暖和!”知青见推不掉,就接过那碗面,挑起一筷面,才吃了一口,又放回桌上,把带的饼干分给大家。大家小小地咬一口饼干,都说没吃过。王家婶妈分到了一块饼干,忙塞到袋里,家里有个三岁的孙子呐。
张家公公摆着手,不接饼干,他蹲下身去,用手掌在知青的鞋上量了量,起身说回家了。
队长来了,坐在知青的床沿上,看着大家高兴,也笑了,说:“我们队有面子,今年,我们大队就分了一个知青,我们队轮上了,挺光荣的。小任同志,以后是一家人了,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对了,他姓任,叫国平,以后大家就叫他小任同志。”
屋里热闹了好长一阵子,深夜,屋面上结霜的时候,大家才陆续回去。
第二天早上,张家公公来敲门,送来一双草蒲鞋,昨夜,他量了鞋码后,回去连夜用稻柴做的,他告诉小任,这东西不怎么好看,但冬天穿着脚不生冻疮。媳妇三婶妈看到后,从旧衣服里理出一把毛线,用针结了二只袜船,这两样东西一配,就是农家高档的过冬鞋了。
不一会儿,阿秀也来了,拿来一条崭新的绒毯:“小任,你的被子薄,这条毛毯借给你。不用还的,我后天就出嫁了,你还小,一个人在外,当心着凉。”
李家婆婆迈着麻雀步,捧着一小瓮腌冬菜,上门就说:“这咸菜,没菜下饭时咬几根,挺下饭的,不馊不坏,慢慢吃。”放下后转身就走,婆婆小时候裹过小脚,走路慢,她怕出工迟到,天天提早出门。
在大队合作医疗室的小慧送来了两个空盐水瓶,还为小任介绍:“晚上倒上热水,放在被窝里,与城里的热水袋一样用。除了大队里的干部,别的人还没给过呢。”
只过了一个晚上,任国平心里就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站在门前,看着低矮破旧的农房,和那群为他奔走的队里人,眼眶里有些湿漉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