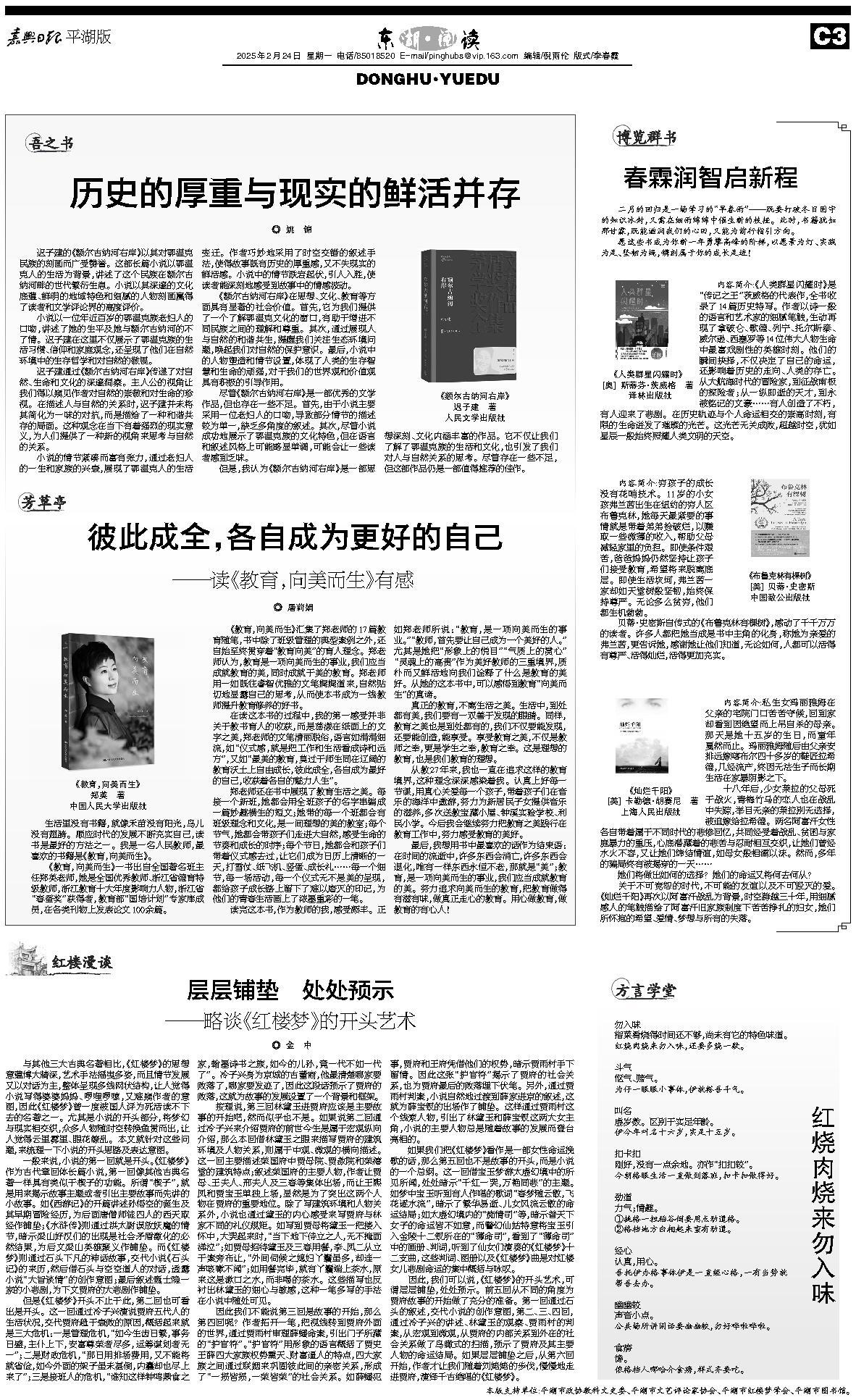金 中
与其他三大古典名著相比,《红楼梦》的思想意蕴博大精深,艺术手法摇曳多姿,而且情节发展又以对话为主,整体呈现多线网状结构,让人觉得小说写得婆婆妈妈、啰哩啰嗦,又难窥作者的意图,因此《红楼梦》曾一度被国人评为死活读不下去的名著之一。尤其是小说的开头部分,将梦幻与现实相交织,众多人物随时空转换鱼贯而出,让人觉得云里雾里、眼花缭乱。本文就针对这些问题,来梳理一下小说的开头思路及表达意图。
一般来说,小说的第一回就是开头。《红楼梦》作为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第一回像其他古典名著一样具有类似于楔子的功能。所谓“楔子”,就是用来揭示故事主题或者引出主要故事而先讲的小故事。如《西游记》的开篇讲述孙悟空的诞生及其早期冒险经历,为后面唐僧师徒四人的西天取经作铺垫;《水浒传》则通过洪太尉误放妖魔的情节,暗示梁山好汉们的出现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为后文梁山英雄聚义作铺垫。而《红楼梦》则通过石头下凡的神话故事,交代小说《石头记》的来历,然后借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透露小说“大旨谈情”的创作意图;最后叙述甄士隐一家的小悲剧,为下文贾府的大悲剧作铺垫。
但是《红楼梦》开头不止于此,第二回也可看出是开头。这一回通过冷子兴演说贾府五代人的生活状况,交代贾府趋于衰败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三大危机:一是管理危机,“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二是财政危机,“那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三是接班人的危机,“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冷子兴身为京城的古董商,他最清楚哪家要败落了,哪家要发迹了,因此这段话预示了贾府的败落,这就为故事的发展设置了一个背景和框架。
按理说,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应该是主要故事的开始吧,然而似乎也不是。如果说第二回通过冷子兴来介绍贾府的前世今生是属于宏观纵向介绍,那么本回借林黛玉之眼来描写贾府的建筑环境及人物关系,则属于中观、微观的横向描述。这一回主要描述荣国府中贾母院、贾赦院和荣禧堂的建筑特点;叙述荣国府的主要人物,作者让贾母、王夫人、邢夫人及三春等集体出场,而让王熙凤和贾宝玉单独上场,显然是为了突出这两个人物在贾府的重要地位。除了写建筑环境和人物关系外,小说也通过黛玉的内心感受来写贾府与林家不同的礼仪规矩。如写到贾母将黛玉一把搂入怀中,大哭起来时,“当下地下侍立之人,无不掩面涕泣”;如贾母招待黛玉及三春用餐,李、凤二从立于案旁布让,“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如用餐完毕,就有丫鬟端上茶水,原来这是漱口之水,而非喝的茶水。这些描写也反衬出林黛玉的细心与敏感,这种一笔多写的手法在小说中随处可见。
因此我们不能说第三回是故事的开始,那么第四回呢?作者拓开一笔,把视线转到贾府外面的世界,通过贾雨村审理薛蟠命案,引出门子所藏的“护官符”。“护官符”用形象的语言概括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权势熏天、财富逼人的特点,四大家族之间通过联姻来巩固彼此间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一损皆损,一荣皆荣”的社会关系。如薛蟠犯事,贾府和王府凭借他们的权势,暗示贾雨村手下留情。因此这张“护官符”揭示了贾府的社会关系,也为贾府最后的败落埋下伏笔。另外,通过贾雨村判案,小说自然地过渡到薛家进京的叙述,这就为薛宝钗的出场作了铺垫。这样通过贾雨村这个线索人物,引出了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大女主角,小说的主要人物总是随着故事的发展而登台亮相的。
如果我们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女性命运挽歌的话,那么第五回也不是故事的开头,而是小说的一个总纲。这一回借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中的所见所闻,处处暗示“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主题。如梦中宝玉听到有人作唱的歌词“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暗示了繁华易逝、儿女风流云散的命运结局;如太虚幻境内的“痴情司”等,暗示普天下女子的命运皆不如意,而警幻仙姑特意将宝玉引入金陵十二钗所在的“薄命司”,看到了“薄命司”中的画册、判词,听到了仙女们演奏的《红楼梦》十二支曲,这些判词、图册以及《红楼梦》曲是对红楼女儿悲剧命运的集中概括与咏叹。
因此,我们可以说,《红楼梦》的开头艺术,可谓层层铺垫,处处预示。前五回从不同的角度为贾府故事的开始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一回通过石头的叙述,交代小说的创作意图,第二、三、四回,通过冷子兴的讲述、林黛玉的观察、贾雨村的判案,从宏观到微观,从贾府的内部关系到外在的社会关系做了鸟瞰式的扫描,预示了贾府及其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局。如果层层铺垫之后,从第六回开始,作者才让我们随着刘姥姥的步伐,慢慢地走进贾府,演绎千古绝唱的《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