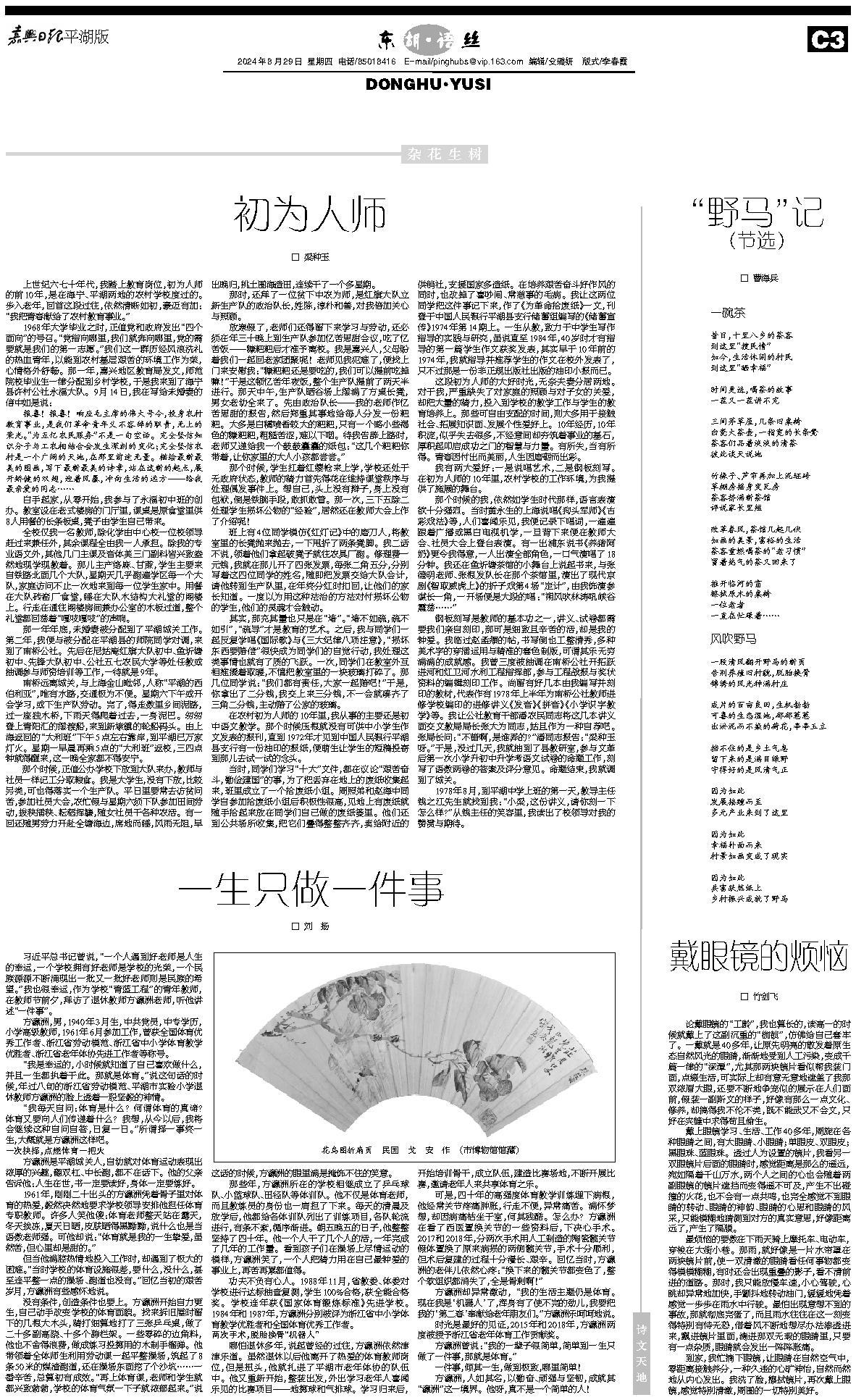□ 梁种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踏上教育岗位,初为人师的前10年,是在海宁、平湖两地的农村学校度过的。步入老年,回首这段过往,依然清晰如初,豪迈有加:“我把青春献给了农村教育事业。”
1968年大学毕业之时,正值党和政府发出“四个面向”的号召。“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第一志愿。”我们这一群历经风浪洗礼的热血青年,以能到农村基层艰苦的环境工作为荣,心情格外舒畅。那一年,嘉兴地区教育局发文,师范院校毕业生一律分配到乡村学校,于是我来到了海宁县许村公社永福大队。9月14日,我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如是说:
报喜!报喜!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令,投身农村教育事业,是我们革命青年义不容辞的职责,无上的荣光。“为五亿农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完全坚信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完全坚信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前途无量。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写下最新最美的诗章,站在这新的起点,展开矫健的双翅,迎着风暴,冲向生活的远方——给我最亲爱的同志……
白手起家,从零开始,我参与了永福初中班的创办。教室设在老式楼房的门厅里,课桌是原食堂里供8人用餐的长条板桌,凳子由学生自己带来。
全校仅我一名教师,除化学由中心校一位校领导赶过来兼任外,其余课程全由我一人承担。除我的专业语文外,其他几门主课及音体美三门副科皆兴致盎然地现学现教着。那儿主产络麻、甘蔗,学生主要来自铁路北面几个大队,星期天几乎跑遍学区每一个大队,家庭访问不止一次地来到每一位学生家中。用餐在大队砖窑厂食堂,睡在大队木结构大礼堂的阁楼上。行走在通往阁楼房间兼办公室的木板过道,整个礼堂都回荡着“嘎吱嘎吱”的声响。
那一年年底,未婚妻被分配到了平湖城关工作。第二年,我便与被分配在平湖县的师院同学对调,来到了南桥公社。先后在尼姑庵红旗大队初中、鱼圻塘初中、先锋大队初中、公社五七农民大学等处任教或抽调参与师资培训等工作,一待就是9年。
南桥远离城关,与上海金山毗邻,人称“平湖的西伯利亚”,唯有水路,交通极为不便。星期六下午或开会学习,或下生产队劳动。完了,得走数里乡间泥路,过一座独木桥,下雨天得爬着过去,一身泥巴。匆匆登上青阳汇的摆渡船,来到新埭镇的轮船码头。由上海返回的“大利班”下午5点左右靠岸,到平湖已万家灯火。星期一早晨再乘5点的“大利班”返校,三四点钟就得醒来,这一晚全家都不得安宁。
那个时候,正值公办学校下放到大队来办,教师与社员一样记工分取粮食。我是大学生,没有下放,比较另类,可也得落实一个生产队。平日里要常去访贫问苦,参加社员大会,农忙假与星期六须下队参加田间劳动,拔秧插秧、耘稻挥镰,随女社员干各种农活。有一回还随男劳力开赴全塘海边,席地而睡,风雨无阻,早出晚归,挑土围海造田,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
那时,还拜了一位贫下中农为师,是红旗大队立新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姓陈,淳朴和善,对我倍加关心与照顾。
放寒假了,老师们还得留下来学习与劳动,还必须在年三十晚上到生产队参加忆苦思甜会议,吃了忆苦饭——糠粑粑后才准予离校。我是嘉兴人,父母盼着我们一起回老家团聚呢!老师见我犯难了,便找上门来安慰我:“糠粑粑还是要吃的,我们可以提前吃掉嘛!”于是这顿忆苦年夜饭,整个生产队提前了两天半进行。那天中午,生产队晒谷场上摆满了方桌长凳,男女老幼全来了。先由政治队长——我的老师作忆苦思甜的报告,然后郑重其事地给每人分发一份粑粑。大多是白糯喷香较大的粑粑,只有一个略小些褐色的糠粑粑,粗糙苦涩,难以下咽。待我告辞上路时,老师又递给我一个鼓鼓囊囊的纸包:“这几个粑粑你带着,让你家里的大人小孩都尝尝。”
那个时候,学生扛着红缨枪来上学,学校还处于无政府状态,教师的精力首先得花在维持课堂秩序与处理偶发事件上。想自己,头上没有辫子,身上没有包袱,倒是铁腕手段,敢抓敢管。那一次,三下五除二处理学生损坏公物的“经验”,居然还在教师大会上作了介绍呢!
班上有4位同学模仿《红灯记》中的磨刀人,将教室里的长凳抛来抛去,一下甩折了两条凳脚。我二话不说,领着他们拿起破凳子就往农具厂跑。修理费一元钱,我就在那儿开了四张发票,每张二角五分,分别写着这四位同学的姓名,随即把发票交给大队会计,请他转到生产队里,在年终分红时扣回,让他们的家长知道。一度以为用这种法治的方法对付损坏公物的学生,他们的灵魂才会触动。
其实,那充其量也只是在“堵”。“堵不如疏,疏不如引”,“疏导”才是教育的艺术。之后,我与同学们一起反复学唱《国际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损坏东西要赔偿”很快成为同学们的自觉行动,我处理这类事情也就有了质的飞跃。一次,同学们在教室外互相推搡着取暖,不慎把教室里的一块玻璃打碎了。那几位同学说:“我们都有责任,大家一起赔吧!”于是,你拿出了二分钱,我交上来三分钱,不一会就凑齐了三角二分钱,主动赔了公家的玻璃。
在农村初为人师的10年里,我从事的主要还是初中语文教学。那个时候压根就没有可供中小学生作文发表的报刊,直到1972年才见到中国人民银行平湖县支行有一份油印的报纸,便萌生让学生的短稿投寄到那儿去试一试的念头。
当时,同学们学习“十大”文件,都在议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事,为了把丢弃在地上的废纸收集起来,班里成立了一个拾废纸小组。周照弟和赵海中同学自参加拾废纸小组后积极性很高,见地上有废纸就随手拾起来放在同学们自己做的废纸篓里。他们还到公共场所收集,把它们叠得整整齐齐,卖给附近的供销社,支援国家多造纸。在培养艰苦奋斗好作风的同时,也改掉了喜吵闹、常惹事的毛病。我让这两位同学把这件事记下来,作了《为革命拾废纸》一文,刊登于中国人民银行平湖县支行储蓄组编写的《储蓄宣传》1974年第14期上。一生从教,致力于中学生写作指导的实践与研究,虽说直至1984年,40岁时才有指导的第一篇学生作文获奖发表,其实早于10年前的1974年,我就指导并推荐学生的作文在校外发表了,只不过那是一份非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油印小报而已。
这段初为人师的大好时光,无奈夫妻分居两地。对于我,严重缺失了对家庭的照顾与对子女的关爱,却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学校的教学工作与学生的教育培养上。那些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则大多用于接触社会、拓展知识面、发展个性爱好上。10年经历,10年积淀,似乎失去很多,不经意间却夯筑着事业的基石,厚积起叩启成功之门的智慧与力量。有所失,当有所得。青春因付出而美丽,人生因磨砺而出彩。
我有两大爱好:一是说唱艺术,二是钢板刻写。在初为人师的10年里,农村学校的工作环境,为我提供了施展的舞台。
那个时候的我,依然如学生时代那样,语言表演欲十分强烈。当时黄永生的上海说唱《狗头军师》《古彩戏法》等,人们喜闻乐见,我便记录下唱词,一遍遍跟着广播或黑白电视机学,一旦背下来便在教师大会、社员大会上登台表演。有一出浦东说书《养猪阿奶》更令我得意,一人出演全部角色,一口气演唱了18分钟。我还在鱼圻塘茶馆的小舞台上说起书来,与张德明老师、张根发队长在那个茶馆里,演出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上》的折子戏第4场“定计”,由我饰演参谋长一角,一开场便是大段的唱:“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
钢板刻写是教师的基本功之一,讲义、试卷都需要我们亲自刻印,那可是细致且辛苦的活,却是我的钟爱。我临过赵孟頫的帖,书写倒也工整清秀,多种美术字的穿插运用与精准的套色制版,可谓其乐无穷满满的成就感。我曾三度被抽调在南桥公社开拓跃进河和红卫河水利工程指挥部,参与工程战报与奖状资料的编辑刻印工作。尚留有好几本由我编写并刻印的教材,代表作有1978年上半年为南桥公社教师进修学校编印的进修讲义《发音》《拼音》《小学识字教学》等。我让公社教育干部潘农民同志将这几本讲义面交文教局局长张大为同志,姑且作为一种自荐吧。张局长问:“不错啊,是谁弄的?”潘同志报告:“梁种玉呀。”于是,没过几天,我就抽到了县教研室,参与文革后第一次小学升初中升学考语文试卷的命题工作,刻写了语数两卷的答案及评分意见。命题结束,我就调到了城关。
1978年8月,到平湖中学上班的第一天,教导主任钱之江先生就找到我:“小梁,这份讲义,请你刻一下怎么样?”从钱主任的笑容里,我读出了校领导对我的赞赏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