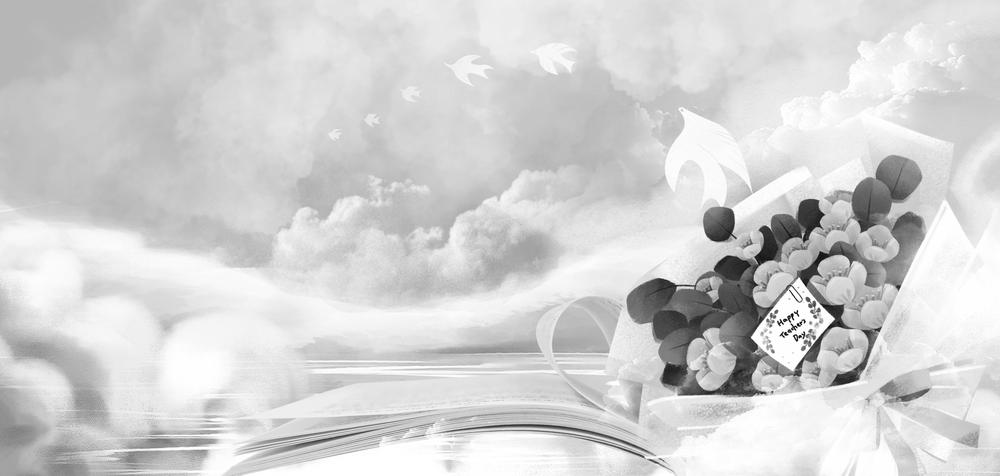“一万步卷帙浩繁的世界,最初,都有良师开卷。”
一起在课堂上探求知识,去操场上找茅茅针,或是互相陪伴度过最辛苦的高三……师生之间的故事一直都在发生,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事情,在今天却显得弥足珍贵。每次打开记忆的大门,往事就会呈现在眼前,当时的喜怒哀乐便会涌上心头,从而激起对老师无限的感激与思念。在第38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一起来看看记忆中那些关于老师的故事……
遁入草叶的时光
——来自一名乡村教师的吟唱
■贾龙弟
教育是需要理想的,扎根农村教育,也是一种理想,是值得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
——题记
十多年前,我参加了朱永新教授发起的新教育实验,我给我的新教育博客取名“草叶”,它源于我所热爱的《草叶集》,一本美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创作的诗集。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语文老师,是乡间的“草叶”,每天忙于备课上课,忙于各种杂务琐事,每天交往的是一群普通的教师,面对的是普通的学生。但我不忘用心写作,我用博客讲述关于他们的普通生活。我相信他们的生活是充满活力的、最真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代表着中国最广大师生的喜怒哀乐。
我知道一名语文教师需要在写作中体会写作的艰辛付出与愉悦收获,要以“草叶”的姿态,迎接每一天普通而有意义的语文生活。我的博文是长满大地的草叶,永远生气蓬勃并散发着诱人的芳香。
其实,我的学生,你们又何尝不是乡间的“草叶”呢?你们普通,你们的父母早出晚归辛劳辗转于每一个可以挣钱的工地、车间,很少有机会关注你们的学习。他们晚上到家,你们已经睡了;你们早上起来,他们已经出去了,你们和父母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你们就像这乡间触目皆是的“草叶”,熟悉又陌生,缺乏关注但仍心存感激,你们理解父母的辛劳,你们同样散发着泥土般的芬芳。
于是,你们和我,组成了我们的“草叶”语文。它少了一份城市的浮躁,多了一分乡村的纯真;少了一份应试的束缚,多了一份成长的自由。
昨天的课堂上,我让你们自由谈论初读毛泽东《沁园春·雪》后的体会,一个男同学说是“豪情”,一位女同学说是“壮丽”,我问“这两者的关系如何”,你们都会心地笑了,说“是情景交融的关系”,我说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你们笑得更欢了。这就是我们的课堂对话,朴实无华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让知识融入生活,让草叶扎根泥土,让欢笑洒满乡间小路。
随心、普通、真实、善良的“草叶”在乡间疯长,琅琅书声飘荡在乡间小路。我和我的学生行走在语文学习的田野上,我们阅读自然,观察最真实的四季变迁,虫鸣鸟语,草木枯荣;我们沉浸自然,抒写我们最真切的自然感受,新旧交替,喜怒哀乐。我们的课堂上有蛙鸣,我们的作文里有花香。
因为“草叶”,我们可以自由地阅读,我们可以真诚地写作,我们可以一起分享“草叶”般的语文。
“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
在农村,土和水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在这基础之上不可遏止地蔓延着的草叶,最具生命力的草叶,我希望它能代表这片土地的心声和呼唤。
乡村里到处都是草叶,我希望自己和学生都能以“草叶”的姿态迎接每一滴清晨的露珠,每一次探索和进步都是一滴露珠,无数的露珠将滋润着生命飞速成长。
是的,我知道,我的“草叶”、我们的语文正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歌唱,我们的航程已经规划,我们的泊船已经起航。“碧波深处有珍奇”,著名语文教育家如是勉励我扎根农村语文教育,我相信,“草叶”的我和我的“草叶”们定会收获沿途的壮丽、神奇与伟大。
偶遇杂感
■夏春燕
跟随着周围欢呼雀跃的脚步,我和儿子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小小的手,圈在我的手里,软乎乎的。九月的天空云淡风轻,阳光斜斜地透过路旁密密层层的香樟树叶子,投影在我们的脸上。
迎面走来了一个高大的身影,在擦肩而过的交会里,他忽然弯下腰来,仔细地辨认着:“您——是夏老师吗?”我从周遭的景物里收回自己的目光,这才发现,面前口罩上方的一双眼睛热烈而赤诚。“是,你是——”“我是XXX,您还记得我吗?”我在脑海里迅速地搜索着与之匹配的信息,可是名字和眼前的脸庞怎么也对不起来。见我犹疑,他又补充道:“我一年级的时候是您教的,您教了我们两年呢。”“哦,对,你就是那个XXX!”我恍然,更惊叹于时光竟然一下子把当年那个小小的身躯变得这么高大!
我们回家的路是一个方向。于是,三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并排走着。他的个子很高,我抬起头也只能够着他肩膀的样子。他告诉我今年高考考取了理想的大学,过几天就要启程了。中途,他对我说:“您知道吗?我一直记得您,您那时候每天都会给我们讲故事,您还会在活动课的时候带我们去操场上找茅茅针,抓昆虫……还有一次,我早饭没吃,您拉着我去办公室给我吃了饼干,您记得吗?”他转过头来微笑地望向我。我的目光有些躲闪,说实在的,他说的这些,我真的不太记得了,都是十几年前发生的、稀松平常的小事。临别的时候,他跟我挥手说:“夏老师,再见!”那么高大的一个男孩子一如小时候那样目光澄澈,充满敬重。
我的内心一阵触动,原来那些在我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在另一个人的眼里是那么与众不同,意义非凡。
我忽然想起不久前的暑假里,偶遇了初一时教我的蔡老师。那日同桌吃饭,我同她说起:“上初中的时候,您送给我一本硬面抄,上面写了一行字,一直激励着我不断进步。”她的目光明显地闪了闪,是不记得了,可能在她几十年的教育生涯里,这样的事情她一直在做。可我却清楚地记得,那年,小学里一向成绩优异的我由于不适应初中紧张的学习节奏,成绩一落千丈,非常苦恼。第一单元语文考试结束后,蔡老师送了我一本硬面抄,扉页上亲笔写了一行字:逐光而行,不惧路长。这本本子我一直珍藏着,以后的很多年里,每当遇到困难,我总会想起这句话,它就像是一束光,给予了我无尽的力量,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妈妈,我们的丁老师会不会带我们去操场上捉虫子呢?”儿子仰起头,对上了我的目光,真诚而期待。在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以后,他的情绪明显地高涨了,声音也高了一个八度:“那么,我希望可以去抓西瓜虫、蚱蜢……”言语间满是希冀。
傍晚的阳光依旧明媚,街道上依旧人影错杂,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生命里出现过的那些熟悉的身影:五年级带我们走进文学殿堂的马老师、六年级课堂里鼓励我的老刘老师、初中时送我硬面抄的蔡老师、大学时给予我无限支持的蒋老师……他们就像一束束温暖的光,照亮了我成长征程里每一圈年轮。是的,这不正是我要努力的方向吗:心中有爱,眼底有光,用心中之爱触动每一颗心灵的美好良善,用眼底之光教会学生捕捉生命里的每一点星光。
他,他们的启蒙
■覃圣勐
说来惭愧,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但是我却不知道他的名字。去年我归乡,十七岁的我遇到七十岁的他,他勉励我好好学习。今年我在外,收到了他病故的消息,于是决定为他写点什么。
二十年前,县里决定为我们村——中国南方偏远地区,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口的山村——建一个小学。村里人依山而居,但是,山在养育村人时,也隔绝了村人通往外界的路。
交通不便加上落后,谁愿意去当这穷地方的老师呢?
他站了出来。
于是,在村子与外界唯一相连的十几里山路上,多了一个身影。他三十岁,不胖不高,但是肩膀很宽厚,眉宇间是单纯的期望。他的手里常常握着一本书,时不时背后还跟着一帮工人,缓慢走入大山,与担着粮食进城的村民相背而行。不多久,一座白墙红瓦的小学,在泥墙灰瓦的村子中拔出尖。
村民们乐于将孩子们送去上学,说是上学,不如说是多了个给他们看管娃儿的地方。有人笑嘻嘻地问:“这小学能干什么?”他笑而不语。全校一名老师,却领着六个年级,几十个孩子。为了方便,他干脆在校内搭了一间小屋,里面三张小板凳,一大一小,一个脚有残缺,他舍不得扔,用来放书。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
围绕村子的大山惊奇地发现,漫山遍野,少了到处撒野的孩子,但是山中鸟兽却因读书声不得安宁。我还记得,当全校师生挤在一间教室上课时,他用握过锄头的手握起粉笔,声音刚硬,一如远处田野弯腰耕耘的农民。
他也关注我们的品德,学校里时不时出现这样一幕,他把戒尺举过头顶,整张脸涨得通红,浑身发抖,对着一个撒谎或者盗窃的小孩,尺堪堪就要落下,却依旧没落下,他气愤地走开,留下一声令人忏悔的叹息。第二天,村里却有传言说谁家孩子又因知错就改受到了表扬。
我也还记得,我在他的教导下,辨认出了父母都不知道的物种,这片大山里没有的物种,而那种得到表扬后的窃喜,到如今我仍时常会想起。大概那时候,知识的种子就已在他的启蒙下播种在我心间了。
这一幕幕在大山里演绎了二十年,孩子们爱戴他,村民也尊敬他。
逢年过节,村民们都会找他写对联,题字。他很乐意做这个,也不收钱。我家就请过他,那是一年春节,他站在桌子前,桌子上摆了一张火红的长宣纸。他一手提笔,一手握着那只手的小臂,双目微眯,落笔,笔走龙蛇。一副对联,他却像是临上战场的将士,竟写出汗来,直到写毕,他才松了一口气。看到工工整整的字,他笑了,听到村民们的赞叹,他的笑容更灿烂了。
几年前,村里通了公路。这本来是件很好的事情,人们不用再徒步越过十几里山路进城了。但是,村民们总是有点恐惧,好像第一个发现雷火的原始人,那是种未知带来的恐惧。他就站在一村人面前,帮他们消除这恐惧。
县里要查户口,他就穿着一件黑色大棉衣挨家挨户问,提建议。县里要土地集中,他还穿着那棉衣跑,一步一步量。当他精疲力尽回家,有村民提着他的棉衣赶上来,笑道:“老师,你把衣服落啦!”那是他仅有的一件御寒的厚衣服。
“这么累干嘛?”夜深人静时,面对这个问题,他总陷入回忆,“我那时候是怎么上学的?每天扛着一袋大米,走了十几里去卖,再走十几里回家,总算能交学费。现在也算个读书人了,但总不希望孩子们也这么累。”想到这里,他起身走到门外,夜空漆黑,但星子闪亮。面对着群山,山中盘曲的公路蜿蜒伸向希望的远方。
这是我印象中的他,作为一名启蒙老师,教学生,教村民,教自己。在不为人知的大山里,演绎着横跨大山的启蒙故事。
老师的鼓励 是孩子最珍贵的礼物
■钱澄蓉
又到一年教师节,很想写点什么,回忆一下我的老师。思索良久,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因为反观自身,如今所拥有的,无论是学识修养,还是处事能力,皆有老师辛勤教育、反复“雕琢”的功劳。9月1日那天,看着幼儿园老师带着小班的小朋友们走进新校园,有的孩子在哭,可老师还是笑着鼓励他们,一双大手牵着小手,一步一步往里走。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老师的鼓励应该是孩子最珍贵的礼物,陪伴孩子走过成长中的风雨。
从小我就是学习“特困生”,特别小的时候,就是班级里学习最差的孩子,后来大一些了,知道“学习要努力”这回事后,开始奋发图强,但也是成绩平平,勉强没有落到最后。我的学习史,也是我向着好学生标准进发的“追赶史”,而其间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老师的身影。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四年级时的数学老师,那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那时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年任教。开学第一周,我就被他喊到办公室,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说,他以几十年的教学经验看,我是可以学好数学的。如今看来,老师是在鼓励教育,但当年的我对这句话极为惊讶,也十分相信。随后那一年,我的数学成绩果然起色不小。大概是摸到了对我的教育方式,此后两年里,两位语文老师也“如法炮制”,在他们鼓励教育的夹持下,我的成绩在小学毕业的时候总算是没有太难看,甚至偶尔还能在文刊上发表几篇小作文。
教育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别看只是老师那么一小句话,甚至是老师批改作业时不经意写上去的一个词,也许都会改变学生的一生。还记得高考前夕,我用尽“洪荒之力”去学习,而成绩却始终在班里排名最后,沮丧的情绪弥漫在周身,一度让我丧失了考试的信心。这一点也被那时的班主任洞悉到了,他找我谈话,跟我分析成绩的好坏、进步与否不能只看班级排名,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他还悄悄联系了我的父母,让父母在家多关注我的心理变化。甚至,在毕业十多年后的同学会上再见,他还在鼓励我:“心态要好,工作生活上的事情都要看开点。”
人们常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而我觉得,老师的鼓励和赏识就是孩子最好的动力。每一个孩子都是在老师的鼓励下慢慢长大的。面对眼前充满好奇和天真的孩子们,老师们总是努力让每一个孩子的心中充满阳光,让每一个孩子在爱的抚慰下快乐成长。老师们总是擅长在孩子的缺点中发现那一点点优点,并用无微不至的爱,呵护着他们生命中的那一点点光!而那一点点不曾被扑灭的光,总有一天会洒成满天的星星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我想,这大概就是教育的伟大、师恩的厚重!
一个微不足道的执念
■方斌杰
现在我的情况就是,成为了教师,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我也不是很确定自己为什么会想当老师,也不记得这条路上哪个老师给过我很强的触动。然而,我会清晰地记得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带给我的执念。
对于初中之前的记忆其实很多都模糊不清了,关于初中的老师,大多记不得什么特殊的事情。唯有初三的班主任,每每想起总令我有一些发凉。中考前的一个礼拜,我沉浸在知道了伯母因患肝癌最多只剩三个月可活的难过之中时,她却斥责我不该在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应该将精力放在中考上。这件不知道对于谁而言确实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直至今日依然是我心头的一道伤痕,也是警醒自己的一把戒尺。
回想起来,我不否认那是一个非常会教书的老师,确实让我当时所在的班级成绩有了提高,而我却总会拿这位班主任跟我高二高三的班主任作对比。关于我高二高三的班主任,一样让我们成绩有所提升,不过我更在意、更难忘的也是她为我们做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们更喜欢叫她海侠姐,一个偶尔是刀子嘴、偶尔又是豆腐嘴,但永远是豆腐心的老师。高二那年的十二月份,大概是因为流行性感冒,班级有近三分之二的同学不是咳嗽就是流涕。上课时,咳嗽声和擤鼻涕声此起彼伏。那会儿时间比较紧,通校生都没什么时间去买药,住校生就更不用说了。海侠姐悄悄地出门,买了十几盒三九感冒灵或是连花清瘟颗粒之类的药,针对不同的症状,也针对没感冒的同学可以预防感冒。同学们没说什么,即使那些平时倔强不肯吃药的也悄悄拿走一点药吃下了。我们什么也没说,我们什么都知道。
至于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海侠姐怎样让傲气的女生明白学习的重要性,怎样让家庭不太好的同学敞开心扉,怎样让冷漠的同学融入这个集体,都是可以写成故事的。更不用说在高三的暑假,一位同学的父亲病故的第二天,她就带着我和班长以及那位同学的好朋友去他家里看望他这件事。即便不是当事人的我,也受到了触动,也受到了治愈。
我上大学后,为海侠姐写了一篇名为《最后一次目送》的故事,里面用了一个同学的一句话:可能刚开始大家都没那么喜欢海侠姐,但最后脑海里满是海侠姐的温柔。我写完那篇故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觉得有什么微不足道的东西在抚摸着那道伤痕,也成了我的一个执念。
大四的时候学校组织实习,当时我带的班上有一个自暴自弃的女生,大概就属于我们所谓的“差生”——上课不听,成绩也非常糟糕。大概是因为跟我年龄差距不大,跟我还能说得来。有一个晚自修,她就准备高一结束去卫校读书这事问问我的意见。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当你成为别人的老师时,你说的话是得经过深思熟虑的,尤其是在这种一对一的场合。我的回答怎样,很可能就会决定她接下来能否看到自己人生的终点。而我能否在那一刻说出最正确的话来引导她,取决于我是否真的希望她过得好,而不是我能不能解决这件“麻烦的事”。
倒不是想说自己初出茅庐就能怎么引导学生走上正途,而是这件事也让我想起了海侠姐,想起了因为她出现在我伤痕上的那个执念。大学毕业后,我接触过一批初中生,他们都很可爱,都各自有各自的想法,我也处理过他们之间不少的矛盾。我知道我对于他们而言,更像一个朋友,更多时候,我也像朋友那样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里化解了问题。
眼下,我即将面对自己的第三批学生,对于他们我可以说一无所知。不过,想到这近十年来时不时浮现的伤痕,我想我多了一点所知,便是我心里对他们必将有那微不足道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