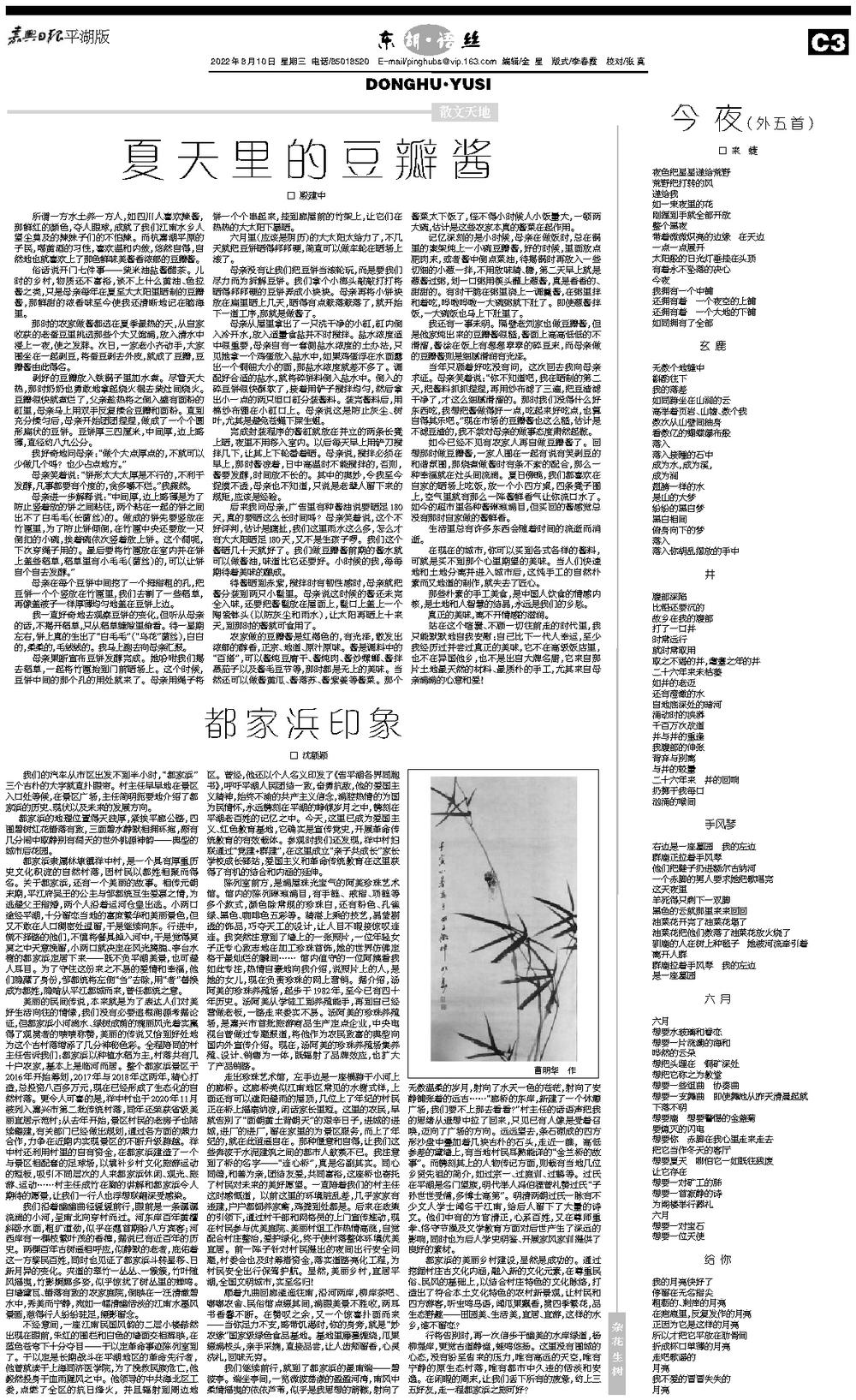□ 殷建中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四川人喜欢辣酱,那鲜红的颜色,夺人眼球,成就了我们江南水乡人望尘莫及的辣妹子们的不怕辣。而杭嘉湖平原的子民,喝黄酒的习性,喜欢温和内敛,悠然自得,自然地也就喜欢上了那色鲜味美酱香浓郁的豆瓣酱。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儿时的乡村,物质还不富裕,谈不上什么黄油、色拉酱之类,只是母亲每年在夏至大太阳里晒制的豆瓣酱,那鲜甜的浓香味至今使我还清晰地记在脑海里。
那时的农家做酱都选在夏季最热的天,从自家收获的老蚕豆里挑选那些个大又饱满,放入清水中浸上一夜,使之发胖。次日,一家老小齐动手,大家围坐在一起剥豆,将蚕豆剥去外皮,就成了豆瓣,豆瓣酱由此得名。
剥好的豆瓣放入铁锅子里加水煮。尽管天大热,那时奶奶也勇敢地拿起烧火棍去柴灶间烧火。豆瓣很快就煮烂了,父亲趁热将之倒入盛有面粉的缸里,母亲马上用双手反复揉合豆瓣和面粉。直到充分揉匀后,母亲开始团团捏捏,做成了一个个圆形扁状的豆饼。豆饼厚三四厘米,中间厚,边上略薄,直径约八九公分。
我好奇地问母亲:“做个大点厚点的,不就可以少做几个吗?也少占点地方。”
母亲笑着说:“饼形太大太厚是不行的,不利于发酵,凡事都要有个度的,贪多嚼不烂。”我赧然。
母亲进一步解释说:“中间厚,边上略薄是为了防止竖着放的饼之间粘住,两个粘在一起的饼之间出不了白毛毛(长菌丝)的。做成的饼先要竖放在竹匾里,为了防止饼倾倒,在竹匾中央还要放一只倒扣的小碗,挨着碗依次竖着放上饼。这个洞呢,下次穿绳子用的。最后要将竹匾放在室内并在饼上盖些稻草,稻草里有小毛毛(菌丝)的,可以让饼自个自去发酵。”
母亲在每个豆饼中间挖了一个拇指粗的孔,把豆饼一个个竖放在竹匾里,我们去割了一些稻草,再像盖被子一样厚薄均匀地盖在豆饼上边。
我一直好奇地去观察豆饼的变化,但听从母亲的话,不揭开稻草,只从稻草缝隙里偷看。待一星期左右,饼上真的生出了“白毛毛”(“乌花”菌丝),白白的,柔柔的,毛绒绒的。我马上跑去向母亲汇报。
母亲果断宣布豆饼发酵完成。她吩咐我们揭去稻草,一起将竹匾抬到门前晒场上。这个时候,豆饼中间的那个孔的用处就来了。母亲用绳子将饼一个个串起来,挂到廊屋前的竹架上,让它们在热热的大太阳下暴晒。
六月里(应该是阴历)的大太阳太给力了,不几天就把豆饼晒得邦邦硬,简直可以做车轮在晒场上滚了。
母亲没有让我们把豆饼当滚轮玩,而是要我们尽力而为拆解豆饼。我们拿个小榔头敲敲打打将晒得邦邦硬的豆饼弄成小块块。母亲再将小饼块放在扁里晒上几天,晒得有点簌落簌落了,就开始下一道工序,那就是做酱了。
母亲从屋里拿出了一只洗干净的小缸,缸内倒入冷开水,放入适量食盐并不时搅拌。盐水浓度适中很重要,母亲自有一套测盐水浓度的土办法,只见她拿一个鸡蛋放入盐水中,如果鸡蛋浮在水面露出一个铜钿大小的面,那盐水浓度就差不多了。调配好合适的盐水,就将碎饼料倒入盐水中。倒入的碎豆饼很快酥软了,接着用铲子搅拌均匀,然后拿出小一点的两只坦口缸分装酱料。装完酱料后,用棉纱布绷在小缸口上。母亲说这是防止灰尘、树叶,尤其是避免苍蝇下屎生蛆。
完成封装程序的酱缸就放在并立的两条长凳上晒,夜里不用移入室内。以后每天早上用铲刀搅拌几下,让其上下轮番着晒。母亲说,搅拌必须在早上,那时酱凉着,日中高温时不能搅拌的,否则,酱要发酵,时间放不长的。其中的奥妙,令我至今捉摸不透,母亲也不知道,只说是老辈人留下来的规矩,应该是经验。
后来我问母亲,广告里有种酱油说要晒足180天,真的要晒这么长时间吗?母亲笑着说,这个不好评判,估计是瞎扯,我们这里雨水这么多,怎么才有大太阳晒足180天,又不是生孩子啰。我们这个酱晒几十天就好了。我们做豆瓣酱前期的酱水就可以做酱油,味道比它还要好。小时候的我,每每期待着美味的酿成。
待酱晒到赤紫,搅拌时有韧性感时,母亲就把酱分装到两只小甏里。母亲说这时候的酱还未完全入味,还要把酱甏放在屋面上,甏口上盖上一个陶瓷钵头(以防灰尘和雨水),让太阳再晒上十来天,到那时的酱就可食用了。
农家做的豆瓣酱是红褐色的,有光泽,散发出浓郁的醇香,正宗、地道、原汁原味。酱是调料中的“百搭”,可以酱炖豆腐干、酱炖肉、酱炒螺蛳、酱拌蒸茄子以及酱毛豆节等,那时都是无上的美味。当然还可以做酱黄瓜、酱落苏、酱紫姜等酱菜。那个酱菜太下饭了,怪不得小时候人小饭量大,一顿两大碗,估计是这些农家本真的酱菜在起作用。
记忆深刻的是小时候,母亲在做饭时,总在锅里的案架炖上一小碗豆瓣酱,好的时候,里面放点肥肉末,或者酱中倒点菜油,待揭锅时再放入一些切细的小葱一拌,不用放味精、糖,第二天早上就是葱酱过粥,划一口粥用筷头蘸上葱酱,真是香香的、甜甜的。有时干脆在粥里浇上一调羹酱,在粥里拌和着吃,哗啦哗啦一大碗粥就下肚了。即使葱酱拌饭,一大碗饭也马上下肚里了。
我还有一事未明。隔壁老刘家也做豆瓣酱,但是他家炖出来的豆瓣酱很糙,酱面上高高低低的不滑溜,酱涂在饭上有窸窸窣窣的碎豆末,而母亲做的豆瓣酱则是细腻滑润有光泽。
当年只顾着好吃没有问, 这次回去我向母亲求证。母亲笑着说:“你不知道吧,我在晒制的第二天,把酱料抓抓捏捏,再用纱布滤了三遍,把豆渣滤干净了,才这么细腻滑溜的。那时我们没得什么好东西吃,我想把酱做得好一点,吃起来好吃点,也算自得其乐吧。”现在市场的豆瓣酱也这么糙,估计是不滤豆渣的,我不禁对母亲的做事态度肃然起敬。
如今已经不见有农家人再自做豆瓣酱了。回想那时做豆瓣酱,一家人围在一起有说有笑剥豆的和谐氛围,那烧煮做酱时有条不紊的配合,那么一种幸福就在灶头间流淌。夏日傍晚,我们都喜欢在自家的晒场上吃饭,放一个小四方桌,四条凳子围上,空气里就有那么一阵酱鲜香气让你流口水了。如今的超市里各种酱琳琅满目,但买回的酱感觉总没有那时自家做的酱鲜香。
生活里总有许多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
在现在的城市,你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酱料,可就是买不到那个心里期望的美味。当人们快速地和土地分离并进入城市后,这纯手工的自然朴素而又地道的制作,就失去了匠心。
那些朴素的手工美食,是中国人饮食的情感内核,是土地和人智慧的结晶,永远是我们的乡愁。
真正的美味,离不开情感的滋润。
站在这个喧嚣、不顾一切往前走的时代里,我只能默默地自我安慰:自己比下一代人幸运,至少我经历过并尝过真正的美味,它不在高级饭店里,也不在异国他乡,也不是出自大牌名厨,它来自那片土地最天然的材料、最质朴的手工,尤其来自母亲满满的心意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