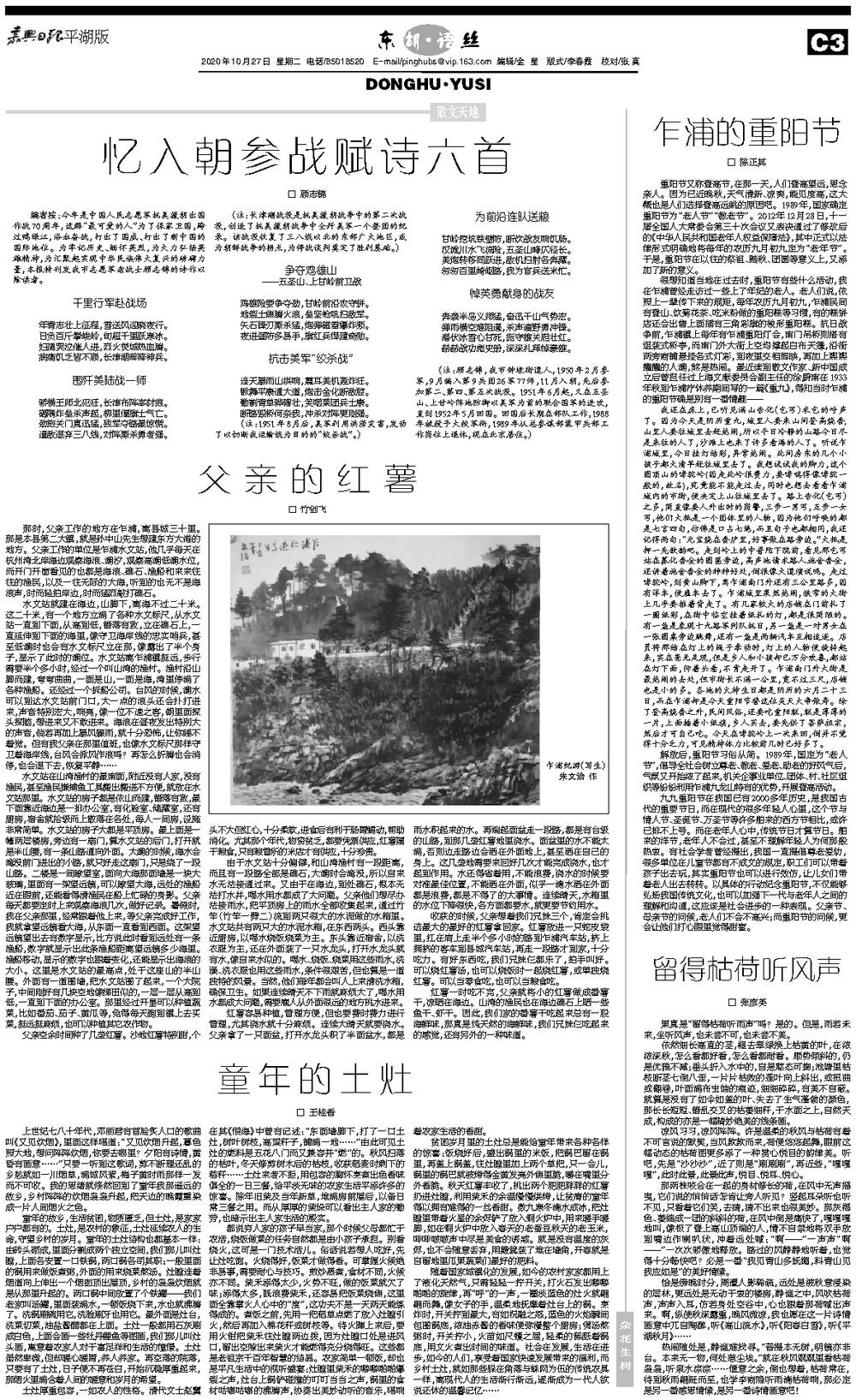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丽君有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叫《又见炊烟》,里面这样唱道:“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只要一听到这歌词,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就如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那样一发而不可收。我的思绪就倏然回到了童年我那遥远的故乡,乡村阵阵的炊烟袅袅升起,把天边的晚霞熏染成一片人间烟火之色。
童年的故乡,生活贫困,物质匮乏,但土灶,是家家户户都有的。土灶,是农村的象征,土灶延续农人的生命,守望乡村的岁月。童年的土灶结构也都基本一样:由砖头砌成,里面分割成两个独立空间,我们那儿叫灶膛,上面各安置一口铁锅,两口锅各司其职:一般里面的锅用来做饭煮粥,外面的用来烧菜熬汤。灶膛连着烟道向上伸出一个烟囱顶出屋顶,乡村的袅袅炊烟就是从那里升起的。两口锅中间放置了个铁罐——我们老家叫汤罐,里面装满水,一顿饭烧下来,水也就沸腾了。洗锅刷碗用它,洗脸刷牙也用它。最外面是灶台,洗菜切菜,油盐酱醋都在上面。土灶一般都用石灰刷成白色,上面会画一些牡丹鲤鱼等图画,我们那儿叫灶头画,寓意着农家人对于富足祥和生活的憧憬。土灶虽然卑微,但却暖心暖胃,养人养家。再空落的院落,只要有了土灶,日子便不再苍白,开始沉稳厚重起来,那烟火里满含着人间的暖意和岁月的希望。
土灶厚重包容,一如农人的性格。清代文士赵翼在其《恨海》中曾有记述:“东面墙脚下,打了一口土灶,树叶树枝,高粱秆子,铺满一地……”由此可见土灶的燃料是五花八门而又兼容并“燃”的。秋风扫落的枯叶,冬天修剪树木后的枯枝,收获稻麦时剩下的秸秆……土灶来者不拒,用包容的胸怀烹煮出色香味俱全的一日三餐,给平淡无味的农家生活平添许多的惊喜。陈年旧柴及当年新草,堆满房前屋后,以备日常三餐之用。而从厚厚的柴垛可以看出主人家的勤劳,也暗示出主人家生活的殷实。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那个时候父母都忙于农活,烧饭做菜的任务自然都是由小孩子承担。别看烧火,这可是一门技术活儿。俗话说若想人吃好,先让灶吃饱。火烧得好,饭菜才做得香。可掌握火候绝非易事,需要耐心与技巧。煎炒蒸煮,食材不同,火候亦不同。柴禾添得太少,火势不旺,做的饭菜就欠了味;添得太多,既浪费柴禾,还容易把饭菜烧焦,这里面全靠掌火人心中的“度”,这功夫不是一天两天能练得成的。煮饭之前,先用一把稻草点燃了放入灶膛引火,然后再加入棉花秆或树枝等。待火蹿上来后,要用火钳把柴禾往灶膛两边拨,因为灶膛口处是进风口,留出空隙出来柴火才能燃得充分烧得旺。这些都是老祖宗千百年智慧的结晶。农家简单一顿饭,却也是平凡生活中的视听盛宴:灶膛里柴禾的噼噼啪啪爆裂之声,灶台上锅铲碰撞的叮叮当当之声,锅里的食材咕嘟咕嘟的沸腾声,协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唱响着农家生活的香甜。
贫困岁月里的土灶总是能给童年带来各种各样的惊喜:饭烧好后,盛出锅里的米饭,把锅巴留在锅里,再盖上锅盖,往灶膛里加上两个草把,只一会儿,锅里的锅巴就被烤得金黄发亮外焦里脆,嚼在嘴里分外香脆。秋天红薯丰收了,挑出两个肥肥胖胖的红薯扔进灶膛,利用柴禾的余温慢慢烘烤,让贫瘠的童年得以拥有难得的一丝香甜。数九寒冬滴水成冰,把灶膛里带着火星的余烬铲了放入铜火炉中,用来暖手暖脚,如在铜火炉中放入春天的老蚕豆秋天的老玉米,哔哔啵啵声中尽是美食的诱惑。就是没有温度的灰烬,也不会随意丢弃,用簸箕装了堆在墙角,开春就是自留地里瓜果蔬菜们最好的肥料。
随着国家城镇化的发展,如今的农村家家都用上了液化天然气,只需轻轻一拧开关,打火石发出噼噼啪啪的旋律,再“呼”的一声,一圈淡蓝色的灶火就翩翩而舞,像女子的手,温柔地抚摩着灶台上的锅。烹炸时,开关拧到最大,有如祝融之怒,蓝色的火焰瞬间包围锅底,浓油赤酱的香味便弥漫整个厨房;煲汤熬粥时,开关拧小,火苗如尺蠖之屈,轻柔的舔舐着锅底,用文火煮出时间的味道。社会在发展,生活在进步,如今的人们,享受着国家快速发展带来的福利,而乡村土灶,就如那些躲在角落与蛛网为伍的传统农具一样,离现代人的生活渐行渐远,逐渐成为一代人欲说还休的温馨记忆……
□ 王桂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