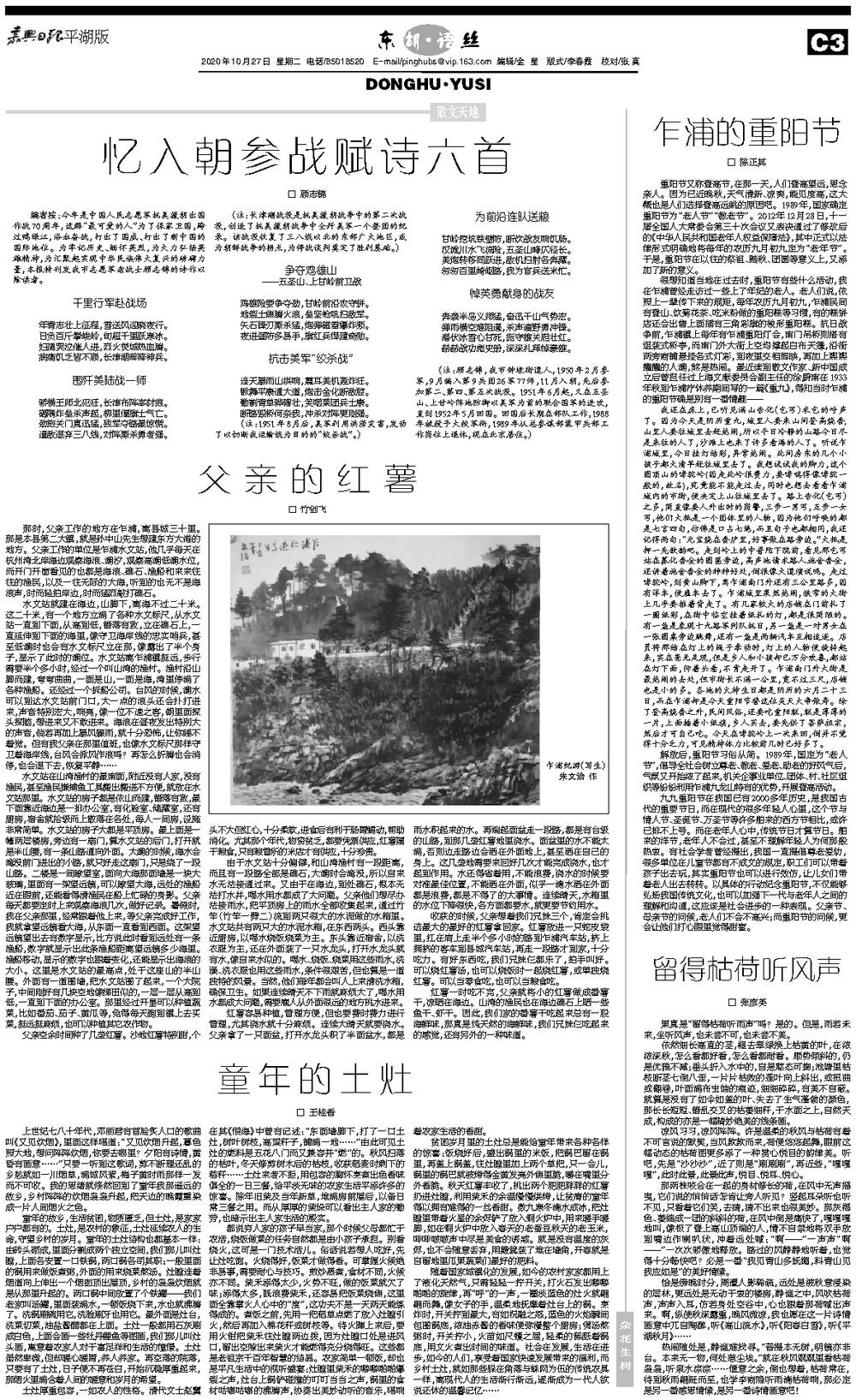□ 竹剑飞
那时,父亲工作的地方在乍浦,离县城三十里。那是本县第二大镇,就是孙中山先生想建东方大港的地方。父亲工作的单位是乍浦水文站,他几乎每天在杭州湾北岸海边观察海浪、潮汐,观察高潮低潮水位,而开门开窗看见的也都是海浪、礁石、渔船和来来往往的渔民,以及一往无际的大海,听到的也无不是海浪声,时而轻拍岸边,时而猛烈敲打礁石。
水文站就建在海边,山脚下,离海不过二十米。这二十米,有一个地方立满了各种水文标尺,从水文站一直到下面,从高到低,错落有致,立在礁石上,一直延伸到下面的海里,像守卫海岸线的忠实哨兵,甚至低潮时也会有水文标尺立在那,像露出了半个身子,显示了此时的潮位。水文站离乍浦镇挺远,步行需要半个多小时,经过一个叫山湾的渔村。渔村沿山脚而建,弯弯曲曲,一面是山,一面是海,湾里停满了各种渔船。还经过一个拆船公司。台风的时候,潮水可以到达水文站前门口,大一点的浪头还会扑打进来,声音特别宏大,响亮,像一位不速之客,朝里面探头探脑,想进来又不敢进来。海浪在昼夜发出特别大的声音,倘若再加上暴风骤雨,就十分恐怖,让你睡不着觉。但有我父亲在那里值班,也像水文标尺那样守卫着海岸线,台风会掀风作浪吗?再怎么折腾也会消停,也会退下去,恢复平静……
水文站在山湾渔村的最南面,附近没有人家,没有渔民,甚至渔民嫌捕鱼工具搬出搬进不方便,就放在水文站那里。水文站的房子都是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最下面靠近海边是一排办公室,有化验室、储藏室,还有厨房,宿舍就拾级而上散落在各处,每人一间房,设施非常简单。水文站的房子大都是平顶房。最上面是一幢两层楼房,旁边有一扇门,算水文站的后门,打开就是半山腰,有一条山路通向外面。大潮的时候,海水会淹没前门进出的小路,就只好走这扇门,只是绕了一段山路。二楼是一间瞭望室,面向大海那面墙是一块大玻璃,里面有一架望远镜,可以瞭望大海,远处的渔船近在眼前,还能看得清渔民在船上忙碌的身影。父亲每天都要定时上来观察海浪几次,做好记录。暑假时,我在父亲那里,经常跟着他上来,等父亲完成好工作,我就拿望远镜看大海,从东面一直看到西面。这架望远镜望出去有数字显示,比方说此时看到远处有一条渔船,数字就显示出此条渔船距离望远镜多少海里。渔船移动,显示的数字也跟着变化,还能显示出海浪的大小。这里是水文站的最高点,处于这座山的半山腰。外面有一道围墙,把水文站围了起来,一个大院子,中间刚好有几块空地像梯田似的,一层一层从高到低,一直到下面的办公室。那里经过开垦可以种植蔬菜,比如番茄、茄子、黄瓜等,免得每天跑到镇上去买菜,挺远挺麻烦,也可以种植其它农作物。
父亲空余时间种了几垄红薯。沙地红薯特别甜,个头不大但红心,十分柔软,进食后有利于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尤其那个年代,物资贫乏,都要凭票供应,红薯属于粮食,只有粮管所的米店才有供应,十分珍贵。
由于水文站十分偏僻,和山湾渔村有一段距离,而且有一段路全部是礁石,大潮时会淹没,所以自来水无法接通过来。又由于在海边,到处礁石,根本无法打水井,喝水用水都成了大问题。父亲他们想尽办法接雨水,把平顶房上的雨水全部收集起来,通过竹竿(竹竿一劈二)流到两只很大的水泥做的水箱里。水文站共有两只大的水泥水箱,在东西两头。西头靠近厨房,以喝水烧饭烧菜为主。东头靠近宿舍,以洗衣服为主,还在外面装了一只水龙头,打开水龙头就有水,像自来水似的。喝水、烧饭、烧菜用这些雨水,洗澡、洗衣服也用这些雨水,条件很艰苦,但也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当然,他们每年都会叫人上来清洗水箱,确保卫生。如果连续晴天不下雨就麻烦大了,喝水用水都成大问题,需要雇人从外面很远的地方挑水进来。
红薯容易种植,管理方便,但也要费时费力进行管理,尤其浇水就十分麻烦。连续大晴天就要浇水。父亲拿了一只面盆,打开水龙头积了半面盆水,都是雨水积起来的水。再端起面盆走一段路,都是有台级的山路,到那几垄红薯地里浇水。面盆里的水不能太满,否则边走路边会洒在外面地上,甚至洒在自己的身上。这几垄地需要来回好几次才能完成浇水,也才起到作用。水还得省着用,不能浪费,浇水的时候要对准最佳位置,不能洒在外面,似乎一滴水洒在外面都是浪费,都是不得了的大事情。连续晴天,水箱里的水位下降很快,各方面都要水,就更要节约用水。
收获的时候,父亲想着我们兄妹三个,肯定会挑选最大的最好的红薯拿回家。红薯放进一只蛇皮袋里,扛在肩上走半个多小时的路到乍浦汽车站,挤上拥挤的客车到县城汽车站,再走一段路才到家,十分吃力。有好东西吃,我们兄妹仨都乐了,拍手叫好。可以烧红薯汤,也可以烧饭时一起烧红薯,或单独烧红薯。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当粮食吃。
红薯一时吃不完,父亲就将小的红薯做成番薯干,凉晒在海边。山湾的渔民也在海边礁石上晒一些鱼干、虾干。因此,我们家的番薯干吃起来总有一股海鲜味,那真是纯天然的海鲜味,我们兄妹仨吃起来的感觉,还有另外的一种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