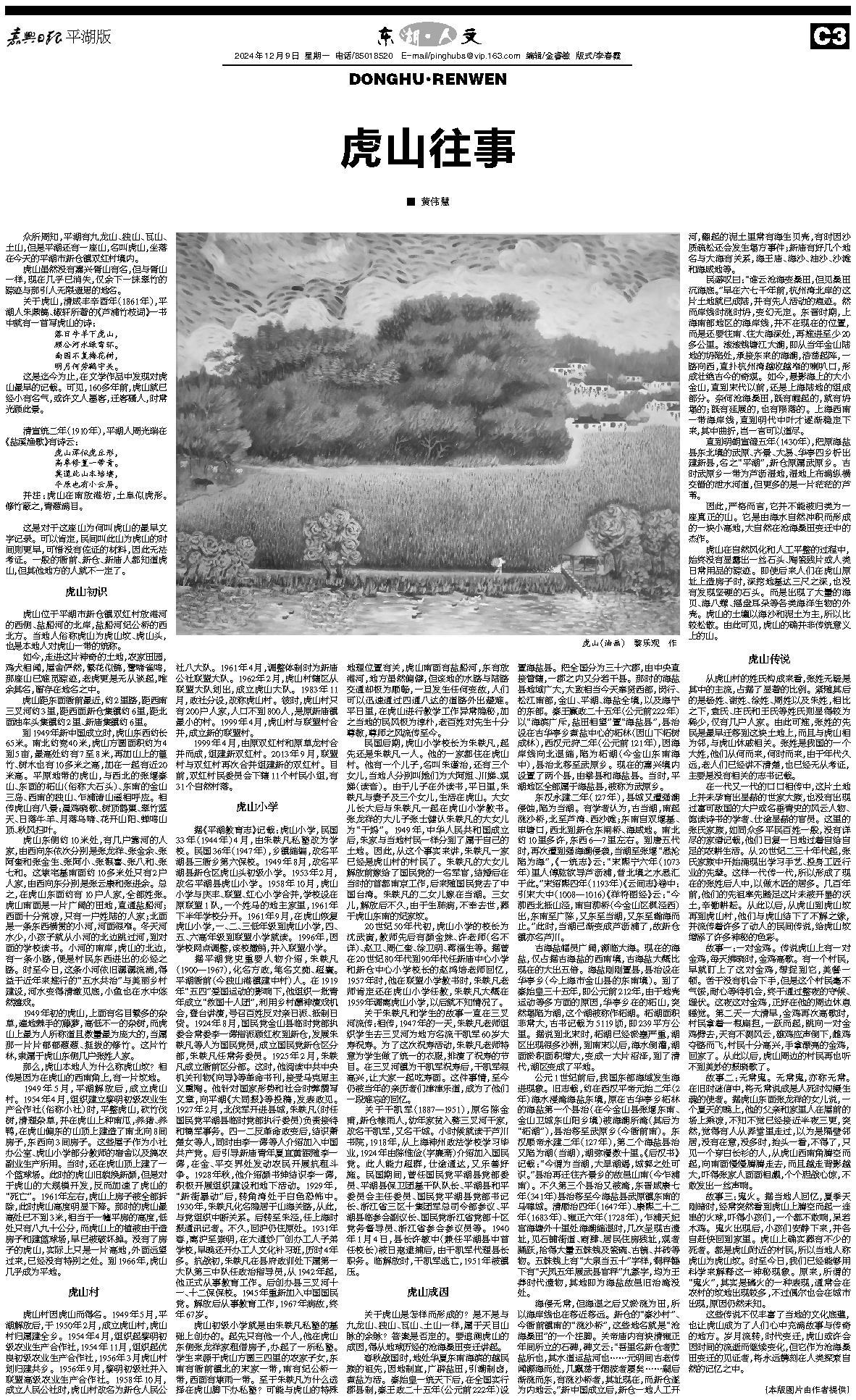虎山初识
虎山(油画) 黎乐观 作
虎山传说
虎山小学
虎山成因
虎山村
众所周知,平湖有九龙山、独山、瓦山、土山,但是平湖还有一座山,名叫虎山,坐落在今天的平湖市新仓镇双红村境内。
虎山虽然没有嘉兴胥山有名,但与胥山一样,现在几乎已消失,仅余下一抹翠竹的踪迹与那引人无限遐思的地名。
关于虎山,清咸丰辛酉年(1861年),平湖人朱鼎镐、椒轩所著的《芦浦竹枝词》一书中就有一首写虎山的诗:
落日牛羊下虎山,
顾公河水绿弯环。
南园不复梅花树,
明月何劳鹤守关。
这是迄今为止,在文学作品中发现对虎山最早的记载。可见,160多年前,虎山就已经小有名气,或许文人墨客,迁客骚人,时常光顾此景。
清宣统二年(1910年),平湖人周光瑞在《盐溪渔歌》有诗云:
虎山浑似虎丘形,
高阜修篁一带青。
莫道此山本培塿,
平原也有小云屏。
并注:虎山在南放港坊,土阜似虎形。修竹蔽之,青葱满目。
这是对于这座山为何叫虎山的最早文字记录。可以肯定,民间叫此山为虎山的时间则更早,可惜没有佐证的材料,因此无法考证。一般的衙前、新仓、新庙人都知道虎山,但其他地方的人就不一定了。
虎山位于平湖市新仓镇双红村放港河的西侧、盐船河的北岸,盐船河纪公桥的西北方。当地人俗称虎山为虎山坟、虎山头,也是本地人对虎山一带的统称。
如今,走进这片神奇的土地,农家田园,鸡犬相闻,屋舍俨然,繁花似锦,鹭啼雀鸣,那座山已难觅踪迹,老虎更是无从谈起,唯余其名,留存在地名之中。
虎山距东面衙前最近,约2里路,距西南三叉河约3里,距西面新仓集镇约6里,距北面油车头集镇约2里、新庙集镇约6里。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虎山东西约长65米。南北约宽40米,虎山方圆面积约为4到5亩,最高处约有7至8米,再加山上的篁竹、树木也有10多米之高,加在一起有近20米高。平原地带的虎山,与西北的张堰秦山、东面的柘山(俗称大石头)、东南的金山三岛、西南的独山、乍浦诸山遥相呼应。相传虎山有八景:晨鸡晓歌、树顶鹊巢、翠竹蓝天、日落牛羊、月落乌啼、花开山阳、蝉鸣山顶、秋风扫叶。
虎山东侧约10米处,有几户靠河的人家,由西向东依次分别是张龙祥、张金余、张阿奎和张金生、张阿小、张银喜、张八和、张七和。这埭宅基南面约10多米处只有2户人家,由西向东分别是张云康和张进余。总之,在虎山东面约有10户人家,全部姓张。虎山南面是一片广阔的田地,直通盐船河;西面十分荒凉,只有一户姓陆的人家;北面是一条东西横贯的小河,河面很窄。冬天河水少,小孩子就从小河的北边跳过河,到对面的学校读书。小河的南岸,虎山的北边,有一条小路,便是村民东西进出的必经之路。时至今日,这条小河依旧潺潺流淌,得益于近年来推行的“五水共治”与美丽乡村建设,河水变得清澈见底,小鱼也在水中悠然嬉戏。
1949年初的虎山,上面有名目繁多的杂草,遍地棘手的藤萝,高低不一的杂树,而虎山上最为人所称道且数量最为庞大的,当属那一片片郁郁葱葱、挺拔的修竹。这片竹林,隶属于虎山东侧几户张姓人家。
那么,虎山本地人为什么称虎山坟?相传是因为在虎山的西南角上,有一片坟地。
1949年5月,平湖解放后,成立虎山村。1954年4月,组织建立黎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俗称小社)时,平整虎山,砍竹伐树,清理杂草,并在虎山上种南瓜,养猪、养鸭,在虎山偏东的山顶上建造了南北向8间房子,东西向3间房子。这些屋子作为小社办公室、虎山小学部分教师的宿舍以及搞农副业生产所用。当时,还在虎山顶上建了一个篮球场。此时的虎山旧貌换新颜,但是对于虎山的大规模开发,反而加速了虎山的“死亡”。1961年左右,虎山上房子被全部拆除,此时虎山高度明显下降。那时的虎山最高处已不到3米,相当于一幢平房的高度,低处只有八九十公分,而虎山上的植被由于造房子和建篮球场,早已被破坏掉。没有了房子的虎山,实际上只是一片高地,外面远望过来,已经没有特别之处。到1966年,虎山几乎成为平地。
虎山村因虎山而得名。1949年5月,平湖解放后,于1950年2月,成立虎山村,虎山村归属建全乡。1954年4月,组织起黎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11月,组织起优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3月虎山村划归建共乡。1956年9月,黎明初级社并入联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10月,成立人民公社时,虎山村改名为新仓人民公社八大队。1961年4月,调整体制时为新庙公社联盟大队。1962年2月,虎山村辖区从联盟大队划出,成立虎山大队。1983年11月,政社分设,改称虎山村。彼时,虎山村只有200户人家,人口不到800人,是原新庙镇最小的村。1999年4月,虎山村与联盟村合并,成立新的联盟村。
1999年4月,由原双红村和原草龙村合并而成,组建新双红村。2013年9月,联盟村与双红村再次合并组建新的双红村。目前,双红村民委员会下辖11个村民小组,有31个自然村落。
据《平湖教育志》记载:虎山小学,民国33年(1944年)4月,由朱轶凡私塾改为学校。民国36年(1947年),乡镇缩编,改名平湖县三衙乡第六保校。1949年8月,改名平湖县新仓区虎山头初级小学。1953年2月,改名平湖县虎山小学。1958年10月,虎山小学与庆丰、联盟、红心小学合并,学校设在原联盟1队,一个姓马的地主家里,1961年下半年学校分开。1961年9月,在虎山恢复虎山小学,一、二、三低年级到虎山小学,四、五、六高年级到联盟小学就读。1996年,因学校网点调整,该校撤销,并入联盟小学。
据平湖党史重要人物介绍,朱轶凡(1900—1967),化名方政,笔名文痴、超寰。平湖衙前(今独山港镇建中村)人。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他组织一批青年成立“救国十人团”,利用乡村酬神演戏机会,登台讲演,号召百姓反对亲日派、抵制日货。1924年8月,国民党金山县临时党部执委会常委李一谔指派顾红枚到新仓,发展朱轶凡等人为国民党员,成立国民党新仓区分部,朱轶凡任常务委员。1925年2月,朱轶凡成立衙前区分部。这时,他阅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等革命书刊,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他针对国家形势和社会时弊撰写文章,向平湖《大同报》等投稿,发表政见。1927年2月,北伐军开进县城,朱轶凡(时任国民党平湖县临时党部执行委员)负责接待和犒军事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结识萧楚女等人,同时由李一谔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引导新庙青年夏宜黄跟随李一谔,在金、平交界处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斗争。1928年秋,他介绍颜书绅结识李一谔,积极开展组织建设和地下活动。1929年,“新街暴动”后,转角湾处于白色恐怖中。1930年,朱轶凡化名隐居于山海关路,从此,与党组织中断关系。后转至朱泾,任上海时报通讯记者。不久,回沪仍住原处。1931年春,离沪至崇明,在大通纱厂创办工人子弟学校,早晚还开办工人文化补习班,历时4年多。抗战初,朱轶凡在县府政训处下属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任政治指导员,从1942年起,他正式从事教育工作。后创办县三叉河十一、十二保保校。1945年重新加入中国国民党。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1967年病故,终年67岁。
虎山初级小学就是由朱轶凡私塾的基础上创办的。起先只有他一个人,他在虎山东侧张龙祥家租借房子,办起了一所私塾。学生来源于虎山方圆三四里的农家子女,东南有衙前镇北的宋家一带,南有纪公桥一带,西面有埭雨一带。至于朱轶凡为什么选择在虎山脚下办私塾?可能与虎山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虎山南面有盐船河,东有放港河,地方虽然偏僻,但该地的水路与陆路交通却极为顺畅,一旦发生任何变故,人们可以迅速通过四通八达的道路外出避难。平日里,在虎山进行教学工作异常隐秘,加之当地的民风极为淳朴,老百姓对先生十分尊敬,尊师之风流传至今。
民国后期,虎山小学校长为朱轶凡,起先还是朱轶凡一人。他的一家都住在虎山村。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朱谨治,还有三个女儿,当地人分别叫她们为大阿姐、川娣、观娣(读音)。由于儿子在外读书,平日里,朱轶凡与妻子及三个女儿,生活在虎山。大女儿长大后与朱轶凡一起在虎山小学教书。张龙祥的大儿子张士健认朱轶凡的大女儿为“干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家与当地村民一样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因此,从这个事实来讲,朱轶凡一家已经是虎山村的村民了。朱轶凡的大女儿解放前嫁给了国民党的一名军官,结婚后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工作,后来随国民党去了中国台湾。朱轶凡的二女儿嫁在当湖。三女儿,解放后不久,由于生肺病,不幸去世,葬于虎山东南的纪家坟。
20世纪50年代初,虎山小学的校长为沈武寅,教师先后有颜金妹、许老师(名不详)、赵卫、周仁奎、徐卫明、蒋福生等。据曾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任新庙中心小学和新仓中心小学校长的赵鸿培老师回忆,1957年时,他在联盟小学教书时,朱轶凡老师肯定还在虎山小学任教,朱轶凡大概在1959年调离虎山小学,以后就不知情况了。
关于朱轶凡和学生的故事一直在三叉河流传:相传,1947年的一天,朱轶凡老师组织学生去三叉河为地方名流干凯军60岁大寿祝寿。为了这次祝寿活动,朱轶凡老师特意为学生做了统一的衣服,排演了祝寿的节目。在三叉河镇为干凯军祝寿后,干凯军很高兴,让大家一起吃寿面。这件事情,至今仍被当年的亲历者们津津乐道,成为了他们一段难忘的回忆。
关于干凯军(1887—1951),原名陈金甫,新仓棣雨人,幼年家贫入赘三叉河干家,改名干凯军,又名干城。小时候就读于芦川书院,1918年,从上海神州政法学校学习毕业,1924年由陈惟俭(字廉斋)介绍加入国民党。此人能力超群,仕途通达,又乐善好施。民国期间,曾任国民党平湖县党部委员、平湖县保卫团基干队队长、平湖县和平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平湖县党部书记长、浙江省三区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议、平湖县临参会副议长、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十区党务督导员、浙江省参会参议员等。1940年1月4日,县长许敏中(兼任平湖县中首任校长)被日寇逮捕后,由干凯军代理县长职务。临解放时,干凯军逃亡,1951年被镇压。
关于虎山是怎样而形成的?是不是与九龙山、独山、瓦山、土山一样,属于天目山脉的余脉?答案是否定的。要追溯虎山的成因,得从地球历经的沧海桑田变迁讲起。
春秋战国时,地处华夏东南海滨的越民族的祖先,因地制宜,广辟盐田,引潮制卤,煮盐为活。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设置海盐县。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由中央直接管辖,一郡之内又分若干县。那时的海盐县地域广大,大致相当今天奉贤西部,闵行、松江南部,金山、平湖、海盐全境,以及海宁的东部。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以“海滨广斥,盐田相望”置“海盐县”,县治设在古华亭乡煮盐中心的柘林(因山下柘树成林),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因海岸线向北退缩,陷为柘湖(今金山东南海中),县治北移至武原乡。现在的嘉兴境内设置了两个县,由拳县和海盐县。当时,平湖地区全部属于海盐县,被称为武原乡。
东汉永建二年(127年),县城又遭强潮侵蚀,陷为当湖。有学者认为,古当湖,南起涨沙桥,北至芦湾、西沙滩;东南自双堰基、申塘口,西北到新仓东闸桥、海咸地。南北约10里多许,东西6—7里左右。到唐五代时,再次遭到强海潮侵袭,当湖至张堰“悉沦陷为海”,《一统志》云:“宋熙宁六年(1073年)里人傅肱欲导芦沥浦,昔北境之水悉汇于此。”宋绍熙四年(1193年)《云间志》卷中:引宋大中(1008—1016)《祥符图经》云:“今泖西北抵山泾,南自泖桥(今金山区枫泾西)出,东南至广陈,又东至当湖,又东至瀚海而止。”此时,当湖己渐变成芦沥浦了,故新仓镇亦名芦川。
古海盐幅员广阔,濒临大海。现在的海盐,仅占据古海盐的西南境,古海盐大概比现在的大出五倍。海盐刚刚置县,县治设在华亭乡(今上海市金山县的东南境)。到了秦始皇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12年,由于地壳运动等多方面的原因,华亭乡在的柘山,突然塌陷为湖,这个湖被称作柘湖。柘湖面积非常大,古书记载为5119顷,即239平方公里。据说到北宋时,柘湖已经淤塞严重,湖区出现很多沙洲,到南宋以后,海水倒灌,湖面淤积面积增大,变成一大片沼泽,到了清代,湖区变成了平地。
公元1世纪前后,我国东部海域发生海进现象。旧志载,约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海水浸淹海盐东境,原在古华亭乡柘林的海盐第一个县治(在今金山县张堰东南、金山卫城东山阳乡境)被海潮所淹(其后为“柘湖”),县治移至武原乡(今衙前南)。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第二个海盐县治又陷为湖(当湖),湖弥漫数十里。《后汉书》记载:“今谓为当湖,大旱湖竭,城郭之处可识。”县治再迁往齐景乡的故邑山南(今乍浦南)。不久第三个县治又被淹,东晋咸康七年(341年)县治移至今海盐县武原镇东南的马嗥城。清顺治四年(1647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雍正六年(1728年),乍浦天妃宫海塘外十里处海潮缩退时,几次呈现古遗址,见石铺街道、商肆、居民住房残址,观者踊跃,拾得大量五铢钱及瓷碗、古镜、井砖等物。五铢钱上有“大泉当五十”字样,铜秤锤下有“天凤五年展武县官秤”九篆字,均为王莽时代遗物,其地即为海盐故邑旧治淹没处。
海侵无常,但海退之后又淤涨为田,所以海岸线也在移近移远。新仓的“秦沙村”、今衙前镇南的“涨沙桥”,这些地名就是“沧海桑田”的一个注脚。关帝庙内有块清雍正年间所立的石碑,碑文云:“吾里名新仓者贮盐所也,其水道运盐河也……元明间古老传闻濒海而处,几飘荡于烟波者屡矣……嗣后渐涨而东,有涨沙桥者,其址现在,而新仓遂为内地云。”新中国成立后,新仓一地人工开河,翻起的泥土里常有海生贝壳,有时因沙质疏松还会发生塌方事件;新庙有好几个地名与大海有关系,海王庙、海沙、油沙、沙滩和海咸地等。
民谣叹曰:“谁云沧海变桑田,但见桑田沉海底。”早在六七千年前,杭州湾北岸的这片土地就已成陆,并有先人活动的痕迹。然而岸线时涨时坍,变幻无定。东晋时期,上海南部地区的海岸线,并不在现在的位置,而是还要往南、往大海深处,再推进至少20多公里。滚滚钱塘江大潮,即从当年金山陆地的坍陷处,承接东来的海潮,浩荡起阵,一路向西,直扑杭州湾越收越窄的喇叭口,形成壮绝古今的奇观。如今,悬影海上的大小金山,直到宋代以前,还是上海陆地的组成部分。奈何沧海桑田,既有崛起的,就有坍塌的;既有延展的,也有陨落的。上海西南一带海岸线,直到明代中叶才逐渐稳定下来,其中曲折,岂一言可以道尽。
直到明朝宣德五年(1430年),把原海盐县东北境的武原、齐景、大易、华亭四乡析出建新县,名之“平湖”,新仓原属武原乡。古时武原乡一带为芦沥湿地,湿地上布满纵横交错的泄水河道,但更多的是一片茫茫的芦苇。
因此,严格而言,它并不能被归类为一座真正的山。它是由海水自然冲积而形成的一块小高地,大自然在沧海桑田变迁中的杰作。
虎山在自然风化和人工平整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显露出一丝石头、陶瓷残片或人类日常用品的踪迹。即使后来人们在虎山原址上造房子时,深挖地基达三尺之深,也没有发现坚硬的石头。而是出现了大量的海贝、海八螺、摇盘耳朵等各类海洋生物的外壳。虎山的土壤以海沙和泥土为主,所以比较松散。由此可见,虎山的确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山。
从虎山村的姓氏构成来看,张姓无疑是其中的主流,占据了显著的比例。紧随其后的是杨姓、谢姓、徐姓、周姓以及朱姓,相比之下,袁氏、庄氏和王氏等姓氏则显得较为稀少,仅有几户人家。由此可推,张姓的先民是最早迁移到这块土地上,而且与虎山相为邻,与虎山休戚相关。张姓是我国的一个大姓,他们从何而来,何时而来,由于年代久远,老人们已经讲不清楚,也已经无从考证,主要是没有相关的志书记载。
在一代又一代的口口相传中,这片土地上并未孕育出显赫的世家大族,也没有出现过富可敌国的大户或名垂青史的风云人物、饱读诗书的学者、仕途显赫的官员。这里的张氏家族,如同众多平民百姓一般,没有详尽的家谱记载,他们日复一日地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张氏家族中开始涌现出学习手艺、投身工匠行业的先辈。这样一代传一代,所以形成了现在的张姓后人中,以做木匠的居多。几百年前,他们的先祖率先踏足这片未被开垦的沃土,辛勤耕耘。从此以后,从虎山到虎山坟再到虎山村,他们与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流传着许多了动人的民间传说,给虎山坟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故事一:一对金鸡。传说虎山上有一对金鸡,每天拂晓时,金鸡高歌。有一个村民,早就盯上了这对金鸡,想捉到它,美餐一顿。苦于没有机会下手,但是这个村民毫不气馁,耐心等待机会,终于通过整夜的守候、埋伏。这夜这对金鸡,正好在他的周边休息睡觉。第二天一大清早,金鸡再次高歌时,村民拿着一根扁担,一跃而起,跳向一对金鸡劈去,天有不测风云,雄鸡应声倒下,雌鸡夺路而飞,村民十分高兴,手拿漂亮的金鸡,回家了。从此以后,虎山周边的村民再也听不到美妙的报晓歌了。
故事二:无常鬼。无常鬼,亦称无常。在旧时迷信中,将无常说成是人死时勾摄生魂的使者。据虎山东面张龙祥的女儿说,一个夏天的晚上,他的父亲和家里人在屋前的场上乘凉,不知不觉已经接近半夜三更,突然,觉得有人从弄堂里走过,以为是隔壁邻居,没有在意,没多时,抬头一看,不得了,只见一个穿白长衫的人,从虎山西南角腾空而起,向南面慢慢腾腾走去,而且越走背影越大,吓得张家人面面相觑,个个胆战心惊,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故事三:鬼火。据当地人回忆,夏季天刚暗时,经常突然看到虎山上腾空而起一连串的火球,吓得小孩们,一个都不敢响,呆若木鸡。鬼火出现后,小孩们安静下来,并各自赶快回到家里。虎山上确实葬有不少的死者。都是虎山附近的村民,所以当地人称虎山为虎山坟。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能够用科学来解释这一神秘现象。原来,所谓的“鬼火”,其实是磷火的一种表现,通常会在农村的坟地出现较多,不过偶尔也会在城市出现,原因仍然未知。
这些传说不仅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底蕴,也让虎山成为了人们心中充满故事与传奇的地方。岁月流转,时代变迁,虎山或许会因时间的流逝而继续变化,但它作为沧海桑田变迁的见证者,将永远镌刻在人类探索自然的记忆之中。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