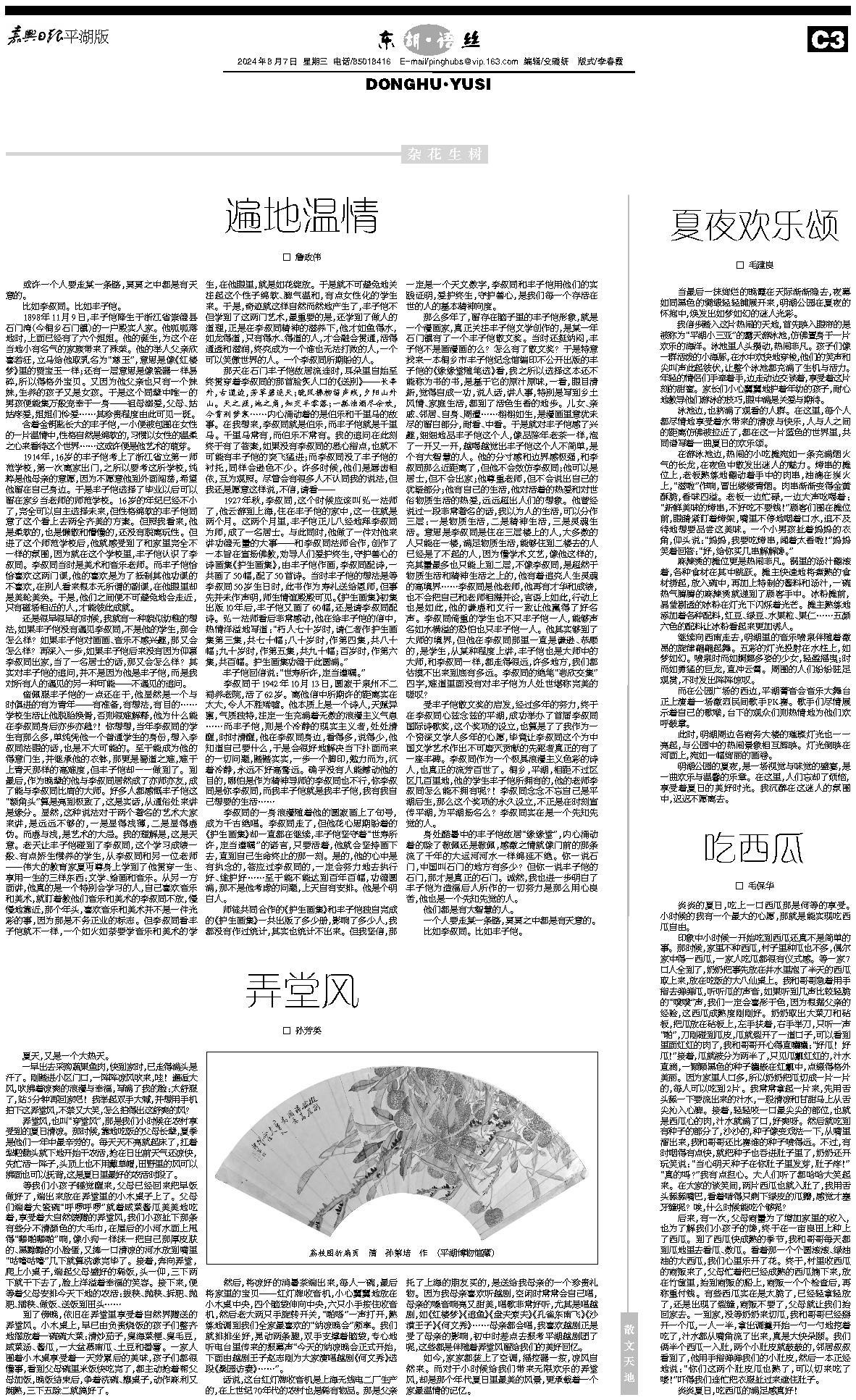□ 詹政伟
或许一个人要走某一条路,冥冥之中都是有天意的。
比如李叔同。比如丰子恺。
1898年11月9日,丰子恺降生于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石门镇)的一户殷实人家。他呱呱落地时,上面已经有了六个姐姐。他的诞生,为这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家族带来了殊荣。他的举人父亲欣喜若狂,立马给他取乳名为“慈玉”,意思是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样;还有一层意思是像瓷器一样易碎,所以得格外宝贝。又因为他父亲也只有一个妹妹,生养的孩子又是女孩。于是这个同辈中唯一的男孩便能集万般宠幸于一身——祖母溺爱,父母、姑姑疼爱,姐姐们怜爱……其珍贵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丰子恺,一小便被包围在女性的一片温情中,性格自然是绵软的,习惯以女性的温柔之心来看待这个世界……这或许便是他艺术的萌芽。
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次离家出门,之所以要考这所学校,纯粹是他母亲的意愿,因为不愿意他到外面闯荡,希望他留在自己身边。于是丰子恺选择了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家乡当老师的师范学校。16岁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完全可以自主选择未来,但性格绵软的丰子恺同意了这个看上去两全齐美的方案。但照我看来,他是柔软的,也是懒散和懵懂的,还没有脱离玩性。但进了这个师范学校后,他就感受到了和家里完全不一样的氛围,因为就在这个学校里,丰子恺认识了李叔同。李叔同当时是美术和音乐老师。而丰子恺恰恰喜欢这两门课,他的喜欢是为了抵制其他功课的不喜欢,在别人看来根本无所谓的副课,在他眼里却是美轮美奂。于是,他们之间便不可避免地会走近,只有磁场相近的人,才能彼此成就。
还是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貌似幼稚的想法,如果丰子恺没有遇见李叔同,不是他的学生,那会怎么样?如果丰子恺对画画、音乐不感兴趣,那又会怎么样?再深入一步,如果丰子恺后来没有因为仰慕李叔同出家,当了一名居士的话,那又会怎么样?其实对丰子恺的追问,并不是因为他是丰子恺,而是我对所有人的遇见的另一种可能——不遇见的追问。
蛮佩服丰子恺的一点还在于,他显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有为青年——有准备,有想法,有目的……学校生活让他脱胎换骨,否则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能在李叔同身后亦步亦趋?!你想想,当年李叔同的学生有那么多,单纯凭他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想入李叔同法眼的话,也是不大可能的。至于能成为他的得意门生,并继承他的衣钵,那更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样的高难度,但丰子恺却一一做到了。到最后,作为晚辈的他与李叔同居然成了亦师亦友,成了能与李叔同比肩的大师。好多人都感慨丰子恺这“额角头”算是亮到极致了,这是实话,从通俗处来讲是缘分。显然,这种说法对于两个著名的艺术大家来讲,是远远不够的,一是显得浅薄,二是显得虚伪。而虚与浅,是艺术的大忌。我的理解是,这是天意。老天让丰子恺碰到了李叔同,这个学习成绩一般、有点娇生惯养的学生,从李叔同和另一位老师——伟大的教育家夏丏尊身上学到了他贯穿一生、享用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从另一方面讲,他真的是一个特别会学习的人,自己喜欢音乐和美术,就盯着教他们音乐和美术的李叔同不放,慢慢地靠近,那个年头,喜欢音乐和美术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因为那是不务正业的标志。但李叔同看丰子恺就不一样,一个如火如荼要学音乐和美术的学生,在他眼里,就是如花绽放。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关注起这个性子绵软、脾气温和,有点女性化的学生来。于是,奇迹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丰子恺不但学到了这两门艺术,最重要的是,还学到了做人的道理,正是在李叔同精神的滋养下,他才如鱼得水,如龙得道,只有得水、得道的人,才会融会贯通,活得通透和滋润,终究成为一个谁也无法打败的人,一个可以笑傲世界的人。一个李叔同所期盼的人。
那天在石门丰子恺故居流连时,耳朵里自始至终贯穿着李叔同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霄别梦寒……内心涌动着的是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在我想来,李叔同就是伯乐,而丰子恺就是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的追问在此刻终于有了答案,如果没有李叔同的悉心指点,也就不可能有丰子恺的突飞猛进;而李叔同没了丰子恺的衬托,同样会逊色不少。许多时候,他们是唇齿相依,互为观照。尽管会有很多人不认同我的说法,但我还是愿意这样说,不信,请看——
1927年秋,李叔同,这个时候应该叫弘一法师了,他云游到上海,住在丰子恺的家中,这一住就是两个月。这两个月里,丰子恺正儿八经地拜李叔同为师,成了一名居士。与此同时,他做了一件对他来讲功德无量的大事——和李叔同法师合作,创作了一本旨在宣扬佛教,劝导人们爱护终生,守护善心的诗画集《护生画集》,由丰子恺作画,李叔同配诗,一共画了50幅,配了50首诗。当时丰子恺的想法是等李叔同50岁生日时,此书作为寿礼送给恩师,但事先并未作声明,师生情谊殷殷可见。《护生画集》初集出版10年后,丰子恺又画了60幅,还是请李叔同配诗。弘一法师看后非常感动,他在给丰子恺的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集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
丰子恺回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李叔同于1942年10月13日,圆寂于泉州不二祠养老院,活了62岁。离他信中所期许的距离实在太大,令人不胜唏嘘。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天赋异禀,气质独特,注定一生充满着无数的浪漫主义气息……而丰子恺,则是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处处清醒,时时清醒,他在李叔同身边,看得多,说得少,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于是会很好地解决当下扑面而来的一切问题,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勉力而为,沉着冷静,永远不好高鹜远。确乎没有人能撼动他的目的,哪怕是作为精神导师的李叔同也不行,你李叔同是你李叔同,而我丰子恺就是我丰子恺,我有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李叔同的一身浪漫随着他的圆寂画上了句号,成为千古绝唱。李叔同走了,但他花心思期盼着的《护生画集》却一直都在继续,丰子恺坚守着“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诺言,只要活着,他就会坚持画下去,直到自己生命终止的那一刻。是的,他的心中是有执念的,答应过李叔同的,一定会努力地去执行好、维护好……至于能不能达到百年百幅,功德圆满,那不是他考虑的问题,上天自有安排。他是个明白人。
师徒共同合作的《护生画集》和丰子恺独自完成的《护生画集》一共出版了多少册,影响了多少人,我都没有作过统计,其实也统计不出来。但我坚信,那一定是一个天文数字,李叔同和丰子恺用他们的实践证明,爱护终生,守护善心,是我们每一个存活在世的人的基本精神向度。
那么多年了,留存在脑子里的丰子恺形象,就是一个漫画家,真正关注丰子恺文学创作的,是某一年石门镇有了一个丰子恺散文奖。当时还挺纳闷,丰子恺不是画漫画的么?怎么有了散文奖?于是特意找来一本桐乡市丰子恺纪念馆编印不公开出版的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选》看,我之所以选择这本还不能称为书的书,是基于它的原汁原味,一看,眼目清新,觉得自成一功,说人话,讲人事,特别是写到乡土风情、家庭生活,都到了活色生香的地步。儿女、亲戚、邻居、自身、周遭……栩栩如生,是漫画里意犹未尽的留白部分,耐看、中看。于是就对丰子恺感了兴趣,细细地品丰子恺这个人,像品陈年老茶一样,泡了一开又一开,越喝越觉出丰子恺这个人不简单,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的分寸感和边界感极强,和李叔同那么近距离了,但他不会效仿李叔同;他可以是居士,但不会出家;他尊重老师,但不会说出自己的犹疑部分;他有自己的生活,他对活着的热爱和对世俗物质生活的热爱,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他曾经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意思是李叔同是住在三层楼上的人,大多数的人只能在一楼,满足物质生活,能够住到二楼去的人已经是了不起的人,因为懂学术文艺,像他这样的,充其量最多也只能上到二层,不像李叔同,是超然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上的,他有着追究人生灵魂的高境界……李叔同是他老师,他再有才华和成绩,也不会把自己和老师相提并论,言语上如此,行动上也是如此,他的谦虚和文行一致让他赢得了好名声。李叔同倚重的学生也不只丰子恺一人,能够声名如水横溢的恐怕也只丰子恺一人。他其实够到了大师的境界,但他在李叔同那里一直是谦逊、恭顺的,是学生,从某种程度上讲,丰子恺也是大师中的大师,和李叔同一样,都走得很远,许多地方,我们都估摸不出来到底有多远。李叔同的绝笔“悲欣交集”四字,难道里面没有对丰子恺为人处世堪称完美的嗟叹?
受丰子恺散文奖的启发,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李叔同心兹念兹的平湖,成功举办了首届李叔同国际诗歌奖,这个奖项的设立,也算是了了我作为一个资深文学人多年的心愿,毕竟让李叔同这个为中国文学艺术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先驱者真正的有了一座丰碑。李叔同作为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也真正的流芳百世了。桐乡,平湖,相距不过区区几百里地,他的学生丰子恺所拥有的,他的老师李叔同怎么能不拥有呢?!李叔同念念不忘自己是平湖后生,那么这个奖项的永久设立,不正是在时刻宣传平湖,为平湖扬名么?李叔同实在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
身处酷暑中的丰子恺故居“缘缘堂”,内心涌动着的除了敬佩还是敬佩,感激之情就像门前的那条流了千年的大运河河水一样绵延不绝。你一说石门,中国叫石门的地方有多少?但你一说丰子恺的石门,那才是真正的石门。诚然,我也进一步明白了丰子恺为造福后人所作的一切努力是那么用心良苦,他也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
他们都是有大智慧的人。
一个人要走某一条路,冥冥之中都是有天意的。
比如李叔同。比如丰子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