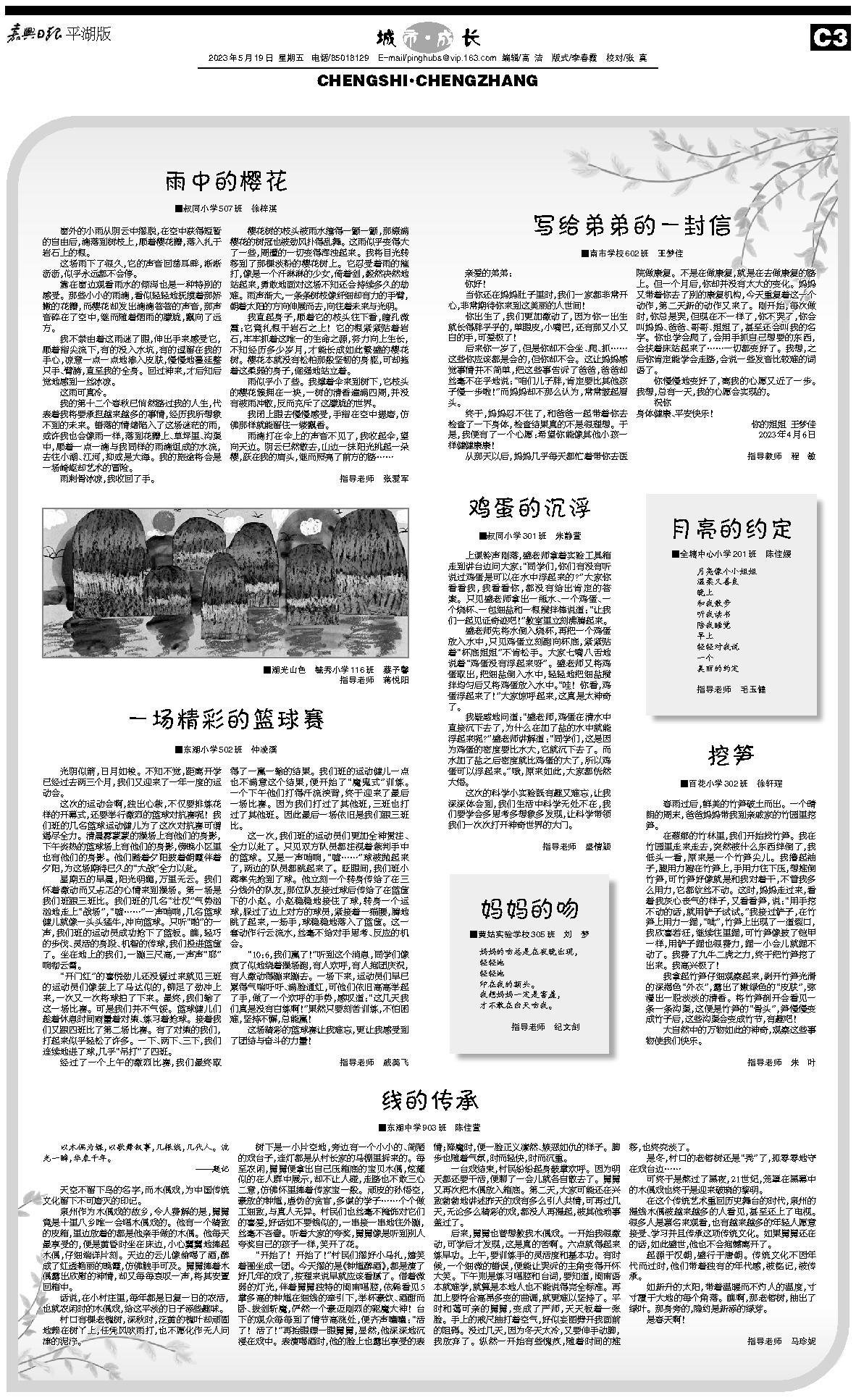■东湖中学903班 陈佳萱
以木偶为媒,以歌舞叙事,几根线,几代人。流光一瞬,华表千年。
——题记
天空不留下鸟的名字,而木偶戏,为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泉州作为木偶戏的故乡,令人费解的是,舅舅竟是十里八乡唯一会唱木偶戏的。他有一个精致的皮箱,里边放着的都是他亲手做的木偶。他每天最享受的,便是黄昏时坐在床边,小心翼翼地捧起木偶,仔细端详片刻。天边的云儿像偷喝了酒,醉成了红透艳丽的晚霞,仿佛触手可及。舅舅捧着木偶露出欣慰的神情,却又每每哀叹一声,将其安置回箱中。
话说,在小村庄里,每年都是日复一日的农活,也就农闲时的木偶戏,给这平淡的日子添些趣味。
村口有棵老槐树,深秋时,泛黄的槐叶却顽固地赖在树丫上,任凭风吹雨打,也不愿化作无人问津的泥泞。
树下是一小片空地,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简陋的戏台子,连灯都是从村长家的马棚里拆来的。每至农闲,舅舅便拿出自己压箱底的宝贝木偶,炫耀似的在人群中展示,却不让人碰,走路也不敢三心二意,仿佛怀里捧着传家宝一般。顽皮的孙悟空,豪放的钟馗,虚伪的贪官,多谋的学子……个个做工细致,与真人无异。村民们也丝毫不掩饰对它们的喜爱,好话如不要钱似的,一串接一串地往外蹦,丝毫不吝啬。听着大家的夸奖,舅舅像是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一样,笑开了花。
“开始了!开始了!”村民们摆好小马扎,嬉笑着围坐成一团。今天摆的是《钟馗醉酒》,都是演了好几年的戏了,按理来说早就应该看腻了。借着微弱的灯光,伴着舅舅独特的闽南唱腔,依稀看见5掌多高的钟馗在细线的牵引下,举杯豪饮、酒酣而卧、拔剑斩魔,俨然一个豪迈刚烈的驱魔大神!台下的观众每每到了情节高涨处,便齐声嚷嚷:“活了!活了!”再抬眼瞟一眼舅舅,显然,他深深地沉浸在戏中。表演喝酒时,他的脸上也露出享受的表情;降魔时,便一脸正义凛然、嫉恶如仇的样子。脚步也随着气氛,时而轻快,时而沉重。
一台戏结束,村民纷纷起身鼓掌欢呼。因为明天都还要干活,便聊了一会儿就各自散去了。舅舅又再次把木偶放入箱底。第二天,大家可能还在兴致勃勃地讲述昨天的戏有多么引人共情,可再过几天,无论多么精彩的戏,都没人再提起,被其他琐事盖过了。
后来,舅舅也曾想教我木偶戏。一开始我很激动,可学后才发现,这是真的苦啊。六点就得起来练早功。上午,要训练手的灵活度和基本功。有时候,一个细微的错误,便能让哭诉的主角变得开怀大笑。下午则是练习唱腔和台词,要知道,闽南语本就难学,就算是本地人也不能说得完全标准。再加上要符合高昂多变的曲调,就更难以坚持了。平时和蔼可亲的舅舅,变成了严师,天天板着一张脸。手上的戒尺抽打着空气,好似妄图劈开我面前的阻碍。没过几天,因为冬天太冷,又要伸手动脚,我放弃了。纵然一开始有些愧疚,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终究淡了。
是冬,村口的老榕树还是“秃”了,孤零零地守在戏台边……
可终于是熬过了黑夜,21世纪,笼罩在黑幕中的木偶戏也终于是迎来破晓的黎明。
在这个传统艺术重回历史舞台的时代,泉州的提线木偶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甚至还上了电视。很多人是慕名来观看,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接受、学习并且传承这项传统文化。如果舅舅还在的话,如此盛世,他也不会抱憾离开了。
起源于汉朝,盛行于唐朝。传统文化不因年代而过时,他们带着独有的年代感,被铭记,被传承。
如新升的太阳,带着温暖而不灼人的温度,寸寸覆于大地的每个角落。瞧啊,那老榕树,抽出了绿叶。那身旁的,隐约是新添的绿芽。
是春天啊!
指导老师 马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