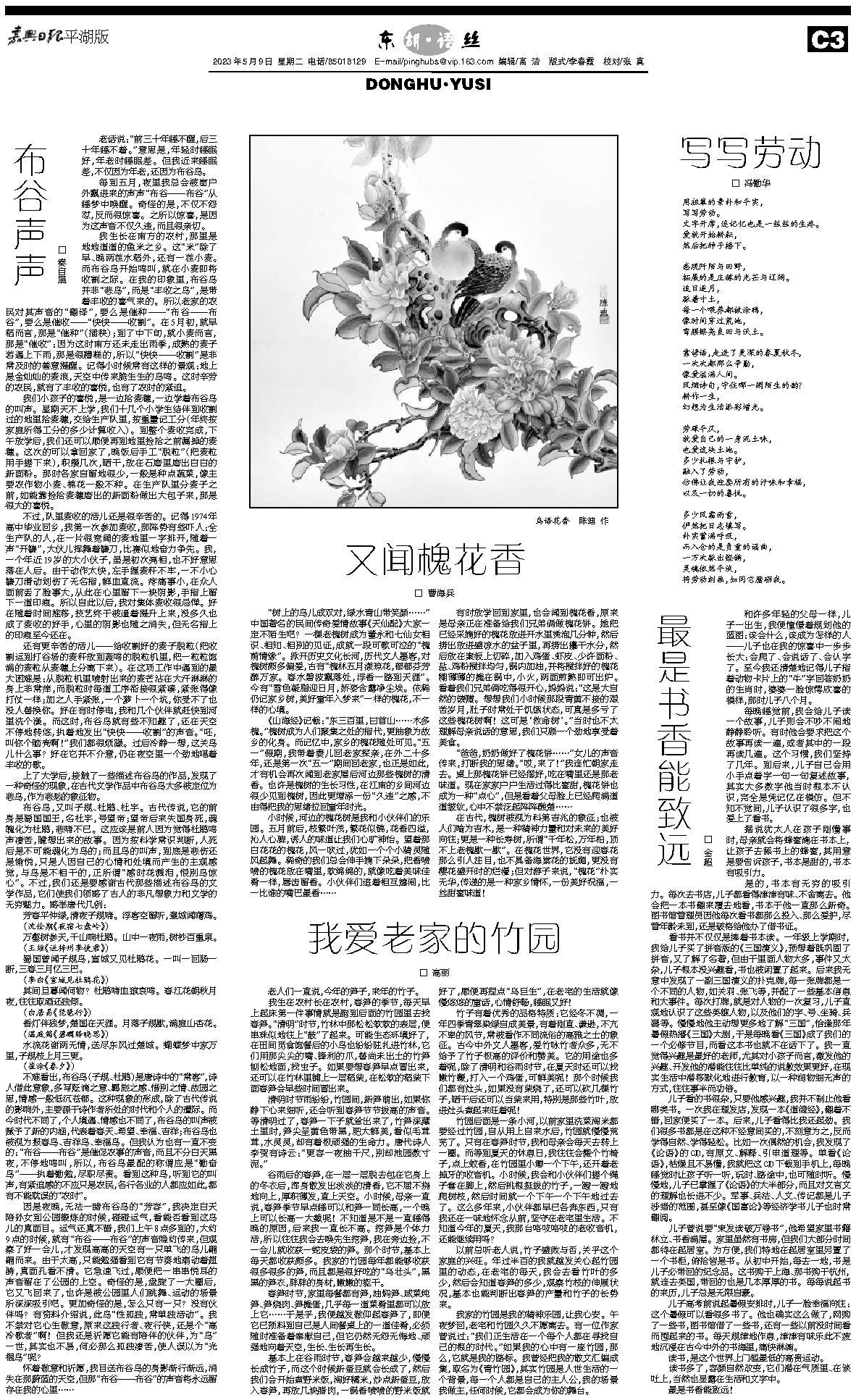□ 秦自黑
老话说:“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意思是,年轻时睡眠好,年老时睡眠差。但我近来睡眠差,不仅因为年老,还因为布谷鸟。
每到五月,夜里我总会被窗户外飘进来的声声“布谷——布谷”从睡梦中唤醒。奇怪的是,不仅不怨怼,反而很惊喜。之所以惊喜,是因为这声音不仅久违,而且很亲切。
我生长在南方的农村,那里是地地道道的鱼米之乡。这“米”除了早、晚两茬水稻外,还有一茬小麦。而布谷鸟开始鸣叫,就在小麦即将收割之际。在我的印象里,布谷鸟并非“悲鸟”,而是“丰收之鸟”,是带着丰收的喜气来的。所以老家的农民对其声音的“翻译”,要么是催种——“布谷——布谷”,要么是催收——“快快——收割”。在5月初,就早稻而言,那是“催种”(插秧);到了中下旬,就小麦而言,那是“催收”:因为这时南方还未走出雨季,成熟的麦子若遇上下雨,那是很糟糕的,所以“快快——收割”是非常及时的善意提醒。记得小时候常有这样的景观:地上是金灿灿的麦浪,天空中传来脆生生的鸟鸣。这时辛劳的农民,就有了丰收的喜悦,也有了农时的紧迫。
我们小孩子的喜悦,是一边拾麦穗,一边学着布谷鸟的叫声。星期天不上学,我们十几个小学生结伴到收割过的地里拾麦穗,交给生产队里,按重量记工分(年终按家庭所得工分的多少计算收入)。到整个麦收完成,下午放学后,我们还可以顺便再到地里捡拾之前漏掉的麦穗。这次的可以拿回家了,晚饭后手工“脱粒”(把麦粒用手搓下来),积攒几次,晒干,放在石磨里磨出白白的新面粉。那时各家自留地很少,一般是种点蔬菜,像主要农作物小麦、棉花一般不种。在生产队里分麦子之前,如能靠捡拾麦穗磨出的新面粉做出大包子来,那是很大的喜悦。
不过,队里麦收的活儿还是很辛苦的。记得1974年高中毕业回乡,我第一次参加麦收,那阵势有些吓人:全生产队的人,在一片很宽阔的麦地里一字排开,随着一声“开镰”,大伙儿挥舞着镰刀,比赛似地奋力争先。我,一个年近19岁的大小伙子,虽是初次亮相,也不好意思落在人后。由于动作太快,左手握麦秆不牢,一不小心镰刀滑动划伤了无名指,鲜血直流。疼痛事小,在众人面前丢了脸事大,从此在心里留下一块阴影,手指上留下一道印痕。所以自此以后,我对集体麦收很忌惮。好在随着时间推移,技艺终于被逼着提升上来,没多久也成了麦收的好手,心里的阴影也随之消失,但无名指上的印痕至今还在。
还有更辛苦的活儿——给收割好的麦子脱粒(把收割运到打谷场的麦秆放到轰鸣的脱粒机里,把一粒粒饱满的麦粒从麦穗上分离下来)。在这项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从脱粒机里喷射出来的麦芒沾在大汗淋淋的身上非常痒,而脱粒时每道工序衔接很紧凑,紧张得像打仗一样;加之人手紧张,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受不了也没人替换你。好在有时停电,我和几个伙伴就赶快到河里洗个澡。而这时,布谷鸟就有些不知趣了,还在天空不停地转悠,执着地发出“快快——收割”的声音。“呸,叫你个脑壳啊!”我们都很烦躁。过后冷静一想,这关鸟儿什么事?好在它并不介意,仍在夜空里一个劲地唱着丰收的歌。
上了大学后,接触了一些描述布谷鸟的作品,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布谷鸟大多被定位为悲鸟,作为悲愁的象征物。
布谷鸟,又叫子规、杜鹃、杜宇。古代传说,它的前身是蜀国国王,名杜宇,号望帝;望帝后来失国身死,魂魄化为杜鹃,悲啼不已。这应该是前人因为觉得杜鹃鸣声凄苦,臆想出来的故事。因为按科学常识判断,人死后是不可能魂化为鸟的;而且鸟的叫声,到底是悲伤还是愉悦,只是人因自己的心情和处境而产生的主观感觉,与鸟是不相干的,正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不过,我们还是要感谢古代那些描述布谷鸟的文学作品,它们使我们领略了古人的非凡想象力和文学的无穷魅力。略举唐代几例:
芳春平仲绿,清夜子规啼。浮客空留听,褒城闻曙鸡。
(沈佺期《夜宿七盘岭》)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王维《送梓州李使君》)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李白《宣城见杜鹃花》)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白居易《琵琶行》)
香灯伴残梦,楚国在天涯。月落子规歇,满庭山杏花。
(温庭筠《碧磵驿晓思》)
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
(崔涂《春夕》)
不难看出,布谷鸟(子规、杜鹃)是唐诗中的“常客”,诗人借此意象,多写贬谪之意、羁旅之感、惜别之情、故园之思,情感一般低沉苍郁。这种现象的形成,除了古代传说的影响外,主要源于诗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的遭际。而今时代不同了,个人境遇、情感也不同了,布谷鸟的叫声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代表着春天、希望、幸福、吉祥;布谷鸟也被视为报春鸟、吉祥鸟、幸福鸟。但我认为也有一直不变的:“布谷——布谷”是催促农事的声音,而且不分白天黑夜,不停地鸣叫,所以,布谷鸟最配的称谓应是“勤奋鸟”——执着勤勉,尽职尽责。看到这种鸟,听到它的叫声,有紧迫感的不应只是农民,各行各业的人都应如此,都有不能耽误的“农时”。
因是夜晚,无法一睹布谷鸟的“芳容”,我决定白天陪孙女到公园锻炼的时候,碰碰运气,看能否看到这鸟儿的真面目。运气还真不错,我们上午8点多到的,大约9点的时候,就有“布谷——布谷”的声音隐约传来,但观察了好一会儿,才发现高高的天空有一只单飞的鸟儿翩翩而来。由于太高,只能勉强看到它有节奏地扇动着翅膀,真面孔看不清。它急速飞过,顺便把一串串悦耳的声音留在了公园的上空。奇怪的是,盘旋了一大圈后,它又飞回来了,也许是被公园里人们跳舞、运动的场景所深深吸引吧。更加奇怪的是,怎么只有一只?没有伙伴吗?有资料介绍说,此鸟“性孤独,常单独活动”。我不禁对它心生敬意,原来这独行者、夜行侠,还是个“高冷歌者”啊!但我还是祈愿它能有陪伴的伙伴,为“鸟”一世,其实也不易,何必那么孤独凄苦,使人误以为“光棍鸟”呢?
怀着敬意和祈愿,我目送布谷鸟的身影渐行渐远,消失在那蔚蓝的天空,但那“布谷——布谷”的声音将永远留存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