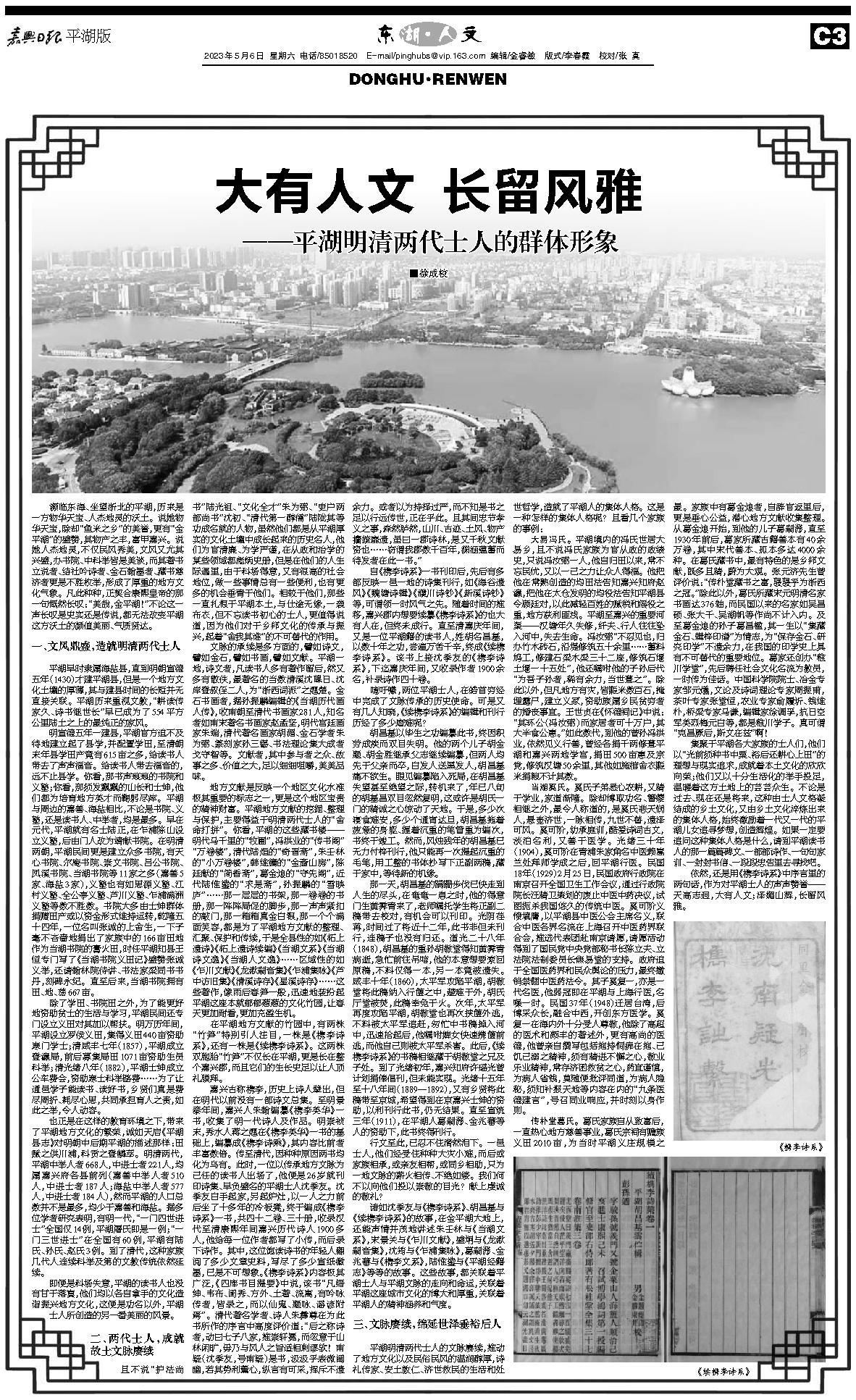——平湖明清两代士人的群体形象
濒临东海、坐望浙北的平湖,历来是一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沃土。说她物华天宝,除却“鱼米之乡”的美誉,更有“金平湖”的盛赞,其物产之丰,富甲嘉兴。说她人杰地灵,不仅民风秀美,文风又尤其兴盛,办书院、中科举皆是美谈,而其著书立说者、结社吟诗者、金石翰墨者、藏书慈济者更是不胜枚举,形成了厚重的地方文化气象。凡此种种,正契合康熙皇帝的那一句慨然长叹:“美哉,金平湖!”不论这一声长叹是史实还是传说,都无法改变平湖这方沃土的颜值美丽、气质贤达。
平湖早时隶属海盐县,直到明朝宣德五年(1430)才建平湖县,但是一个地方文化土壤的厚薄,其与建县时间的长短并无直接关联。平湖历来重视文教,“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早已成为了554平方公里陆土之上的最纯正的家风。
明宣德五年一建县,平湖官方迫不及待地建立起了县学,并配置学田,至清朝末年县学田产竟有615亩之多,给读书人带去了声声福音。给读书人带去福音的,远不止县学。你看,那书声琅琅的书院和义塾;你看,那须发飘飘的山长和士绅,他们都为培育地方英才而鞠躬尽瘁。平湖与周边的嘉善、海盐相比,不论是书院、义塾,还是读书人、中举者,均是最多。早在元代,平湖就有名士陆正,在乍浦陈山设立义塾,后由门人改为靖献书院。在明清两朝,平湖民间更是建立众多书院,有天心书院、尔庵书院、崇文书院、吕公书院、凤溪书院、当湖书院等11家之多(嘉善5家、海盐3家),义塾也有如思源义塾、江村义塾、全公亭义塾、芦川义塾、乍浦满洲义塾等数不胜数。书院大多由士绅群体捐赠田产或以资金形式维持运转,乾隆五十四年,一位名叫张诚的上舍生,一下子毫不吝啬地捐出了家族中的166亩田地作为当湖书院的膏火田,时任平湖知县王恒专门写了《当湖书院义田记》盛赞张诚义举,还请翰林院侍讲、书法家梁同书书丹,刻碑永纪。直至后来,当湖书院拥有田、地、荡667亩。
除了学田、书院田之外,为了能更好地资助贫士的生活与学习,平湖民间还专门设立义田对其加以帮扶。明万历年间,平湖设立罗侯义田,集得义田440亩资助寒门学士;清咸丰七年(1857),平湖成立登瀛局,前后募集局田1071亩资助生员科举;清光绪八年(1882),平湖士绅成立公车费会,资助寒士科举路费……为了让通邑学子能读书、读好书,乡贤们真是费尽周折、耗尽心思,共同承担育人之责,如此之举,令人动容。
也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带来了平湖地方文化的繁荣,诚如天启《平湖县志》对明朝中后期平湖的描述那样:田赋之供川浦,科贡之登鳞萃。明清两代,平湖中举人者668人,中进士者221人,均属嘉兴府各县前列(嘉善中举人者510人,中进士者187人;海盐中举人者577人,中进士者184人),然而平湖的人口总数并不是最多,均少于嘉善和海盐。据多位学者研究表明,有明一代,“一门四世进士”全国仅14例,平湖屠氏即是一例;“一门三世进士”在全国有60例,平湖有陆氏、孙氏、赵氏3例。到了清代,这种家族几代人连续科举及第的文教传统依然延续。
即便是科场失意,平湖的读书人也没有甘于落寞,他们均以各自拿手的文化造诣振兴地方文化,这便是功名以外,平湖士人所创造的另一番美丽的风景。
且不说“护法尚书”陆光祖、“文化全才”朱为弼、“吏户两部尚书”沈初、“清代第一醇儒”陆陇其等功成名就的人物,虽然他们都是从平湖厚实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历史名人,他们为官清廉、为学严谨,在从政和治学的某些领域都彪炳史册,但是在他们的人生际遇里,由于科场得意,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做一些事情总有一些便利,也有更多的机会垂青于他们。相较于他们,那些一直扎根于平湖本土,与仕途无缘,一袭布衣,但不忘读书初心的士人,更值得说道,因为他们对于乡邦文化的传承与振兴,起着“舍我其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脉的承续是多方面的,譬如诗文,譬如金石,譬如书画,譬如文献。平湖一地,诗文者,凡读书人多有著作留后,然又多有散佚,最著名的当数清溪沈皞日、沈岸登叔侄二人,为“浙西词派”之翘楚。金石书画者,据孙振麟编辑的《当湖历代画人传》,收南朝至清代书画家281人,知名者如南宋著名书画家赵孟坚,明代宫廷画家朱端,清代著名画家胡湄、金石学者朱为弼、篆刻家孙三锡、书法理论集大成者戈守智等。文献者,其中参与者之众、故事之多、价值之大,足以细细咀嚼,美美品味。
地方文献是反映一个地区文化水准极其重要的标志之一,更是这个地区宝贵的精神财富。平湖地方文献的挖掘、整理与保护,主要得益于明清两代士人的“舍命打拼”。你看,平湖的这些藏书楼——明代马千里的“牧圃”,冯洪业的“传书阁”“万卷楼”,清代陆烜的“奇晋斋”,朱壬林的“小万卷楼”,韩维镛的“金齑山房”,陈廷献的“简香斋”,葛金烺的“守先阁”,近代陆惟鍌的“求是斋”,孙振麟的“雪映庐”……那一层层的书架,那一卷卷的书册,那一阵阵局促的脚步,那一声声紧扣的敲门,那一箱箱真金白银,那一个个满面笑容,都是为了平湖地方文献的整理、汇聚、保护和传续,于是全县性的如《柘上遗诗》《柘上遗诗续编》《当湖文系》《当湖诗文逸》《当湖人文逸》……区域性的如《乍川文献》《龙湫嗣音集》《乍浦集咏》《芦中访旧集》《清溪诗存》《星溪诗存》……这些著作,像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地装扮起平湖这座本就郁郁葱葱的文化竹园,让春天更加耐看,更加充盈生机。
在平湖地方文献的竹园中,有两株“竹笋”特别引人注目,一株是《槜李诗系》,还有一株是《续槜李诗系》。这两株双胞胎“竹笋”不仅长在平湖,更是长在整个嘉兴郡,而且它们的生长史足以让人顶礼膜拜。
嘉兴古称槜李,历史上诗人辈出,但在明代以前没有一部诗文总集。至明景泰年间,嘉兴人朱翰编纂《槜李英华》一书,收集了明一代诗人及作品。明崇祯末,秀水人蒋之翘在《槜李英华》一书的基础上,编纂成《槜李诗乘》,其内容比前者丰富数倍。传至清代,因种种原因两书均化为乌有。此时,一位以传承地方文脉为己任的读书人出场了,他便是26岁就刊印诗集、早负盛名的平湖士人沈季友。沈季友白手起家,另起炉灶,以一人之力前后坐了十多年的冷板凳,终于编成《槜李诗系》一书,共四十二卷、三十册,收录汉代至清康熙年间嘉兴历代诗人1900多人,他给每一位作者都写了小传,而后录下诗作。其中,这位饱读诗书的年轻人翻阅了多少文章史料,写尽了多少宣纸徽墨,已是不可想象。《槜李诗系》内容极其广泛,《四库书目提要》中说,该书“凡缙绅、韦布、闺秀、方外、土著、流寓,有吟咏传者,皆录之,而以仙鬼、题咏、谣谚附焉”。清代著名学者、诗人朱彝尊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高度评价道:“后之称诗者,动曰七子八家,推崇轩冕,而忽意于山林闲旷,毋乃与风人之旨适相刺谬欤!南疑(沈季友,号南疑)是书,汲汲乎表微阐幽,若其势利薰心,纵言有可采,挥斥不遗余力。或者以为持择过严,而不知是书之足以行远传世,正在乎此。且其间忠节孝义之事,森然胪然,山川、古迹、土风、物产攟摭靡遗,虽曰一郡诗林,是又千秋文献资也……窃谓我郡数千百年,渊涵蕴蓄而待发者在此一书。”
自《槜李诗系》一书刊印后,先后有多部反映一邑一地的诗集刊行,如《海谷遗风》《魏塘诗辑》《濮川诗钞》《新溪诗钞》等,可谓领一时风气之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嘉兴郡内想要续纂《槜李诗系》的也大有人在,但终未成行。直至清嘉庆年间,又是一位平湖籍的读书人,姓胡名昌基,以数十年之功,尝遍万苦千辛,终成《续槜李诗系》。该书上接沈季友的《槜李诗系》,下迄嘉庆年间,又收录作者1900余名,补录诗作四十卷。
噫吁嚱,两位平湖士人,在皓首穷经中完成了文脉传承的历史使命。可是又有几人知晓,《续槜李诗系》的编辑和刊行历经了多少磨难呢?
胡昌基以毕生之功编纂此书,终因积劳成疾而双目失明。他的两个儿子胡金题、胡金胜继承父志继续编纂,但两人均先于父亲而卒,白发人送黑发人,胡昌基痛不欲生。眼见编纂陷入死局,在胡昌基失望甚至绝望之际,转机来了,年已八旬的胡基昌双目忽然复明,这或许是胡氏一门的精诚之心惊动了天地。于是,多少次寝食难安,多少个通宵达旦,胡昌基拖着疲惫的身躯、握着沉重的笔管重为编次,书终于竣工。然而,风烛残年的胡昌基已无力付梓刊行,他只能再一次提起沉重的毛笔,用工整的书体抄写下正副两稿,藏于家中,等待新的机缘。
那一天,胡昌基的蹒跚步伐已快走到人生的尽头,在奄奄一息之时,他的得意门生黄霁青来了,老师嘱托学生将正副二稿带去校对,有机会可以刊印。光阴荏苒,时间过了将近十二年,此书非但未刊行,连稿子也没有归还。道光二十八年(1848),胡昌基的重孙胡敬堂得知黄霁青病逝,急忙前往吊唁,他的本意想要索回原稿,不料仅得一本,另一本竟被遗失。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平湖,胡敬堂将此稿纳入行箧之中,避难于外,胡氏厅堂被焚,此稿幸免于火。次年,太平军再度攻陷平湖,胡敬堂也再次挟箧外逃,不料被太平军追赶,匆忙中书稿掉入河中,迅速拾起后,他嘱咐婢女快速携箧前逃,而他自己则被太平军杀害。此后,《续槜李诗系》的书稿相继藏于胡敬堂之兄及子处。到了光绪初年,嘉兴知府许瑶光曾计划捐俸倡刊,但未能实现。光绪十五年至十八年间(1889—1892),又有乡贤将此稿带至京城,希望得到在京嘉兴士绅的资助,以利刊行此书,仍无结果。直至宣统三年(1911),在平湖人葛嗣浵、金兆蕃等人的资助下,此书终得刊行。
行文至此,已忍不住潸然泪下。一邑士人,他们经受住种种大灾小难,而后或家族相承,或亲友相帮,或同乡相助,只为一地文脉的薪火相传、不绝如缕。我们何不以向他们投以崇敬的目光?献上虔诚的敬礼?
诸如沈季友与《槜李诗系》、胡昌基与《续槜李诗系》的故事,在金平湖大地上,还能声情并茂地讲述朱壬林与《当湖文系》,宋景关与《乍川文献》,盛坰与《龙湫嗣音集》,沈筠与《乍浦集咏》,葛嗣浵、金兆蕃与《檇李文系》,陆惟鍌与《平湖经籍志》等等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关联着平湖士人与平湖文脉的走向和命运,关联着平湖这座城市文化的博大和厚重,关联着平湖人的精神涵养和气度。
平湖明清两代士人的文脉赓续,推动了地方文化以及民俗民风的温润醇厚,诗礼传家、安土敦仁、济世救民的生活和处世哲学,造就了平湖人的集体人格。这是一种怎样的集体人格呢?且看几个家族的事例:
大易冯氏。平湖境内的冯氏世居大易乡,且不说冯氏家族为官从政的政绩史,只说冯汝弼一人,他自归田以来,常不忘民忧,又以一己之力让众人得福。他把他在常熟创造的均田法告知嘉兴知府赵瀛,把他在太仓发明的均役法告知平湖县令顾廷对,以此减轻百姓的赋税和徭役之重,地方获利匪浅。平湖至嘉兴的重要河渠——汉塘年久失修,纤夫、行人往往坠入河中,失去生命。冯汝弼“不忍见也,归办竹木砖石,沿堤修筑五十余里……蓄料鸠工,修建石梁木梁三十二座,修筑石堰土堰一十五处”,他还嘱咐他的子孙后代“为吾子孙者,稀有余力,当世葺之”。除此以外,但凡地方有灾,皆赈米数百石,掩埋露尸,建立义冢,资助族属乡民贫穷者的婚丧事宜。王世贞在《怀德祠记》中说:“其环公(冯汝弼)而家居者可十万户,其大半食公惠。”如此数代,到他的曾孙冯洪业,依然见义行善,曾经各捐千两修葺平湖和嘉兴两地学宫,捐田500亩惠及宗党,修筑汉塘50余里,其他如施棺舍衣赈米捐粮不计其数。
当湖奚氏。奚氏子弟悉心农耕,又精于学业,家道渐隆。除却博取功名、簪缨相继之外,最令人称道的,是奚氏悲天悯人,悬壶济世,一脉相传,九世不替,遗泽可风。奚可阶,幼承庭训,酷爱诗词古文,淡泊名利,又善于医学。光绪三十年(1904),奚可阶在青浦朱家角名中医赖嵩兰处拜师学成之后,回平湖行医。民国18年(1929)2月25日,民国政府行政院在南京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通过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策划的废止中医中药决议,试图扼杀我国悠久的传统中医。奚可阶义愤填膺,以平湖县中医公会主席名义,联合中医各界名流在上海召开中医药界联合会,推选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请愿活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立法院法制委员长焦易堂的支持。政府迫于全国医药界和民众舆论的压力,最终撤销禁锢中医药法令。其子奚复一,亦是一代名医,他弱冠即在平湖与上海行医,名噪一时。民国37年(1948)迁居台湾,后博采众长,融合中西,开创东方医学。奚复一在海内外十分受人尊敬,他除了高超的医术和颇丰的著述外,更有高尚的医德,他曾亲自撰写包括抱持恫瘝在抱、己饥己溺之精神,须有精进不懈之心,敬业乐业精神,常存济困救贫之心,药宜谨慎,为病人省钱,莫随便批评同道,为病人隐秘,须知补报天地等内容在内的“九条医德建言”,号召同业响应,并时刻以身作则。
传朴堂葛氏。葛氏家族自从致富后,一直热心地方慈善事业,葛氏宗祠有赡族义田2010亩,为当时平湖义庄规模之最。家族中有葛金烺者,自辞官返里后,更是垂心公益,潜心地方文献收集整理。从葛金烺开始,到他的儿子葛嗣浵,直至1930年前后,葛家所藏古籍善本有40余万卷,其中宋代善本、孤本多达4000余种。在葛氏藏书中,最有特色的是乡邦文献,既多且精,蔚为大观。张元济先生曾评价说:“传朴堂藏书之富,骎骎乎为浙西之冠。”除此以外,葛氏所藏宋元明清名家书画达376轴,而民国以来的名家如吴昌硕、张大千、吴湖帆等作尚不计入内。及至葛金烺的孙子葛昌楹,其一生以“集藏金石、辑梓印谱”为情志,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不遗余力,在我国的印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葛家还创办“稚川学堂”,先后聘任社会文化名流为教员,一时传为佳话。中国科学院院士、冶金专家邹元燨,文论及诗词理论专家周振甫,茶叶专家张堂恒,农业专家俞履圻、钱维朴,桥梁专家马谦,编辑家徐调孚,抗日空军英烈梅元白等,都是稚川学子。真可谓“克昌厥后,斯文在兹”啊!
集聚于平湖各大家族的士人们,他们以“光前须种书中粟、裕后还耕心上田”的理想与现实追求,成就着本土文化的欣欣向荣;他们又以十分生活化的举手投足,温暖着这方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种由士人文格凝结成的乡土文化,又由乡土文化淬炼出来的集体人格,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平湖儿女追寻梦想,创造辉煌。如果一定要追问这种集体人格是什么,请到平湖读书人的那一篇篇碑文、一部部诗作、一句句家训、一封封书信、一段段忠告里去寻找吧。
依然,还是用《槜李诗系》中序言里的两句话,作为对平湖士人的声声赞誉——天高志迥,大有人文;泽媚山辉,长留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