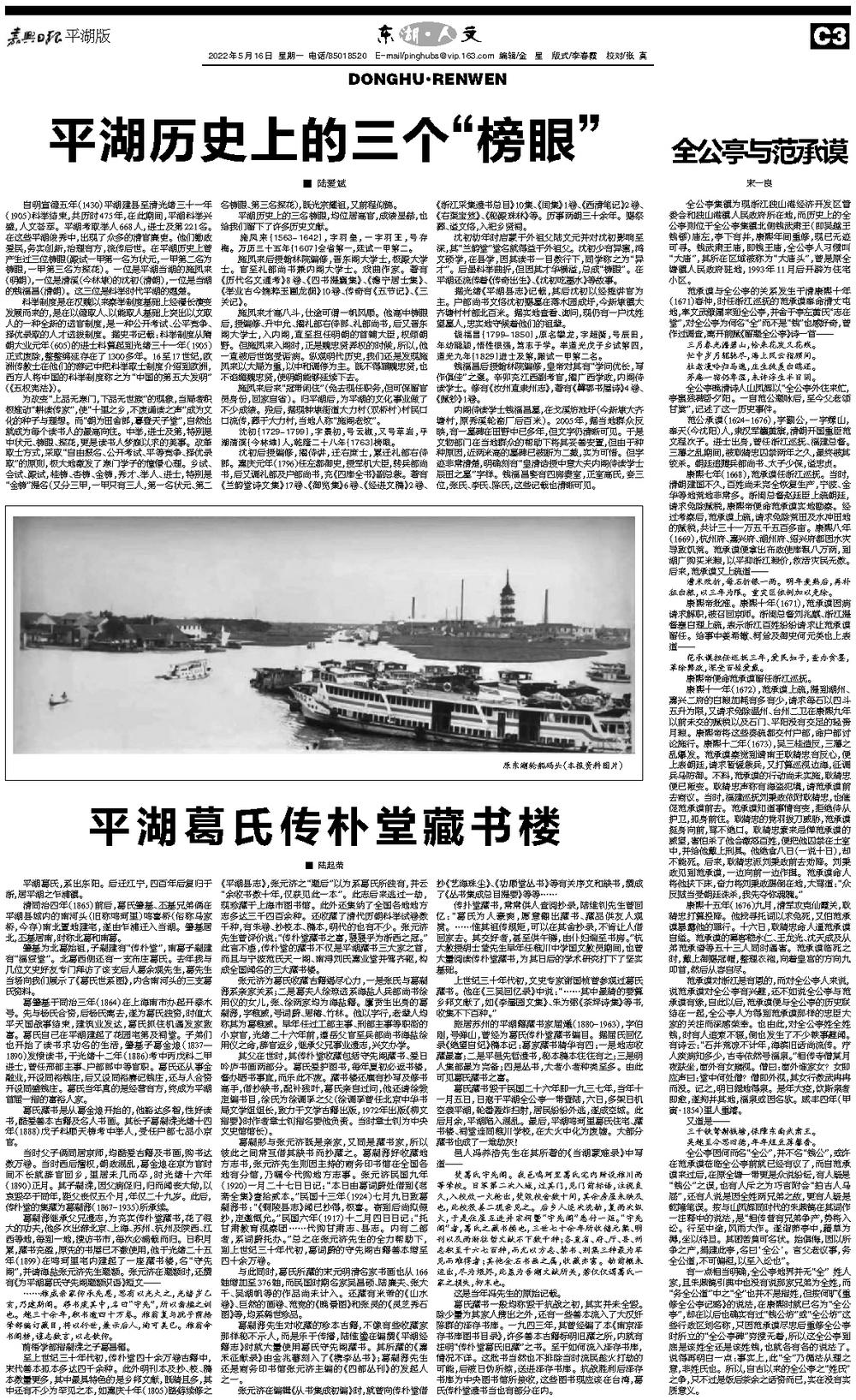宋一良
全公亭集镇为现浙江独山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独山港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而历史上的全公亭则位于全公亭集镇北侧钱武肃王(即吴越王钱镠)庙左,亭下有井,康熙年间重修,现已无迹可寻。钱武肃王庙,即钱王庙,全公亭人习惯叫“大庙”,其所在区域被称为“大庙头”,曾是原全塘镇人民政府驻地,1993年11月后开辟为住宅小区。
范承谟与全公亭的关系发生于清康熙十年(1671)春仲,时任浙江巡抚的范承谟奉命清丈屯地,率文武僚属来到全公亭,并舍于亭左黄氏“志在堂”,对全公亭为何名“全”而不是“钱”也感好奇,曾作过调查,离开前赋《留题全公亭》诗一首——
三月春光澹碧山,恰来花发又花残。
忙中岁月驱驰尽,海上风云指顾间。
杜老漫呤归马逸,庄生徒羡白鸥还。
茅庵一宿仍卑湿,未许浮生半日闲。
全公亭晚清诗人山凤辉以“全公亭外往来忙,亭裹残碑卧夕阳。一自范公题咏后,至今父老颂甘棠”,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
范公承谟(1624-1676),字觐公,一字螺山,奉天(今沈阳)人,隶汉军镶黄旗,清朝开国重臣范文程次子。进士出身,曾任浙江巡抚、福建总督。三藩之乱期间,被耿精忠囚禁两年之久,最终被其绞杀。朝廷追赠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谥忠贞。
康熙七年(1668),范承谟任浙江巡抚。当时,清朝建国不久,百姓尚未完全恢复生产,宁波、金华等地荒地非常多。浙闽总督赵廷臣上疏朝廷,请求免除赋税,康熙帝便命范承谟实地勘察。经过考察后,范承谟上疏,请求免除荒田及水冲田地的赋税,共计三十一万五千五百多亩。康熙八年(1669),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绍兴府都因水灾导致饥荒。范承谟便拿出布政使库银八万两,到湖广购买米粮,以平抑浙江粮价,救活灾民无数。后来,范承谟又上疏道——
漕米改折,每石折银一两。明年麦熟后,再补征白粮,以三年为限。重灾区依例加以免除。
康熙帝批准。康熙十年(1671),范承谟因病请求解职,被召回京师。浙闽总督刘兆麒、浙江提督塞白理上疏,表示浙江百姓纷纷请求让范承谟留任。给事中姜希辙、柯耸及御史何元英也上表道——
范承谟担任巡抚三年,爱民如子,查办贪墨,革除弊政,深受百姓爱戴。
康熙帝便命范承谟留任浙江巡抚。
康熙十一年(1672),范承谟上疏,提到湖州、嘉兴二府的白粮加耗有多有少,请求每石以四斗五升为限,又请求免除温州、台州二卫在康熙九年以前未交的赋税以及石门、平阳没有交足的轻赍月粮。康熙帝将这些奏疏都交付户部,命户部讨论施行。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造反,三藩之乱爆发。范承谟察觉到靖南王耿精忠有反心,便上表朝廷,请求暂缓裁兵,又打算巡视边海,征调兵马防御。不料,范承谟的行动尚未实施,耿精忠便已叛变。耿精忠声称有海盗犯境,请范承谟前去商议。当时,福建巡抚刘秉政依附耿精忠,也催促范承谟前去。范承谟知道事情有变,拒绝侍从护卫,孤身前往。耿精忠的党羽拔刀威胁,范承谟挺身向前,骂不绝口。耿精忠素来忌惮范承谟的威望,害怕杀了他会激怒百姓,便把他囚禁在土室中,并给他戴上刑具。他绝食八日(一说十日),却不能死。后来,耿精忠派刘秉政前去劝降。刘秉政见到范承谟,一边向前一边作揖。范承谟命人将他扶下床,奋力将刘秉政踢倒在地,大骂道:“众反贼当受朝廷诛杀,我先夺你魂魄。”
康熙十五年(1676)九月,清军攻克仙霞关,耿精忠打算投降。他找寻托词以求免死,又怕范承谟暴露他的罪行。十六日,耿精忠命人逼范承谟自缢。范承谟的幕客嵇永仁、王龙光、沈天成及从弟范承谱等五十三人同时遇害。范承谟临死之时,戴上御赐冠帽,整理衣袍,向着皇宫的方向九叩首,然后从容自尽。
范承谟对浙江是有恩的,而对全公亭人来说,说范承谟对全公亭有兴趣,还不如说全公亭与范承谟有缘,自此以后,范承谟便与全公亭的历史联结在一起,全公亭人为得到范承谟那样的忠臣大家的关注而深感荣幸。也由此,对全公亭姓全姓钱,时有人追索不辍,倒也发生了不少轶事趣闻。有诗云:“石井荒凉不计年,海滨旧话尚流传。疗人疾病知多少,古寺依然号福泉。”相传寺僧某月夜趺坐,窗外有女窥视。僧曰:窗外谁家女?女即应声曰:堂中何处僧?僧即外视,其女行数武冉冉而没。记之,明日掘地得泉。是年大疫,饮斯泉者即愈,遂拘井其地,福泉或因名欤。咸丰四年(甲寅·1854)里人重濬。
又道是——
三千铁弩射钱塘,保障东南武肃王。
吴越至今思旧德,年年俎豆荐馨香。
全公亭因何而名“全公”,并不名“钱公”,或许在范承谟莅临全公亭前就已经有议了,而自范承谟来过后,在原全塘一带更是众说纷纭,有人疑是“钱公”之误,也有人斥之为巧言附会“拍古人马屁”,还有人说是因全姓两兄弟之故,更有人疑是乾隆笔误。按与山凤辉同时代的朱鼎镐在其词作一注释中的说法,是“相传昔有兄弟争产,势将入讼。行至中途,风雨大作。遂诣茆亭中,藉草为褥,坐以待旦。其困苦莫可名状。始俱悔,因以所争之产,捐建此亭,名曰‘全公’。言父老议事,务全公道,不可偏袒,以至入讼也”。
有一点相当明确,全公亭地界并无“全” 姓人家,且朱鼎镐引典中也没有说那家兄弟为全姓,而“务全公道”中之“全”也并不是指姓,但按何旷《重修全公亭记略》的说法,在康熙时就已名为“全公亭”,却在以后也确实有过“钱公坊”或“全公坊”这些行政区划名称,只因范承谟尽忠后重修全公亭时所立的“全公亭碑”穷搜无着,所以这全公亭到底是该姓全还是该姓钱,也就各有各的说法了。说得再明白一点:事实上,此“全”乃循法从理之意,非姓氏也。所以,自古以来的全公亭之“姓氏”之争,只不过是饭后茶余之话资而已,实在没有实质意义。